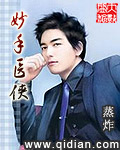陈玄丘清楚,殷受虽在他的影响之下,性格改变了许多。而且殷受对姬侯并无感情,不会因为姬侯优柔寡断。
但朝中受姬侯蒙蔽的大臣很多,这其中却不乏能影响到殷受的人,比如首相沐衍、亚相简登隆,这都是当过太子老师的人。
只有他在场,殷受才有主心骨,于是不敢怠慢,立即吩咐备马,要立刻入宫。
待陈玄丘来到前院,却见八个灰袍剑士,背负长剑,傲然而立。
陈玄丘一瞧那服色,便是一怔:“奉常寺的人,他们怎么在这?”
门廊下,玉衡负着双手,悠然走了出来,微笑道:“昨日贵府出了刺客,国君担心大夫的安全,所以命我奉常寺派人护从大夫,玉某请缨,担了这一差使。”
陈玄丘受宠若惊地道:“玉少祝身份贵重,竟然为陈某担当护从职责,实不敢当啊。”
玉衡道:“无妨。昨日离开尊府时,玉某也受了那人袭击,一个随从被她害死。太祝的意思是,籍由大夫你,或许可以钓出她来。”
原来是以我为饵……
陈玄丘摸了摸鼻子,不再自作多情了。
……
后宅里边,娜扎和妲己并肩站在那儿,眼见陈玄丘头也不回地走了,直到陈玄丘身影消失,妲己这才担心地道:“他是不是生气了?”
娜扎道:“他不会那么小气吧?“
妲己道:“可你看,他一路走,头都没回过。”
娜扎道:“又不是生死离别,他回头作什么?”
“也是喔。”妲己拍拍胸膊儿:“那我就放心了。”
娜扎乜视着妲己,道:“所以呢,不用盖他的房子了是吧?”
妲己苦恼地道:“我都规划好了的,再给他盖一间,很挤的。”
娜扎想了想,很没义气地道:“也是,现在我们俩住,正好。”
两个人贼兮兮地互相看看,妲己不放心地道:“真不给他盖啊,会不会显得我们很不厚道?”
娜扎想了想,忽然灵机一动:“要不……咱俩给他造一栋树屋?把房子吊在树上,哎呀,就是鸟巢啦,也不算太破坏园中景致。”
妲己不放心地道:“可我,光会设计,我不会造房子啊。”
娜扎撇嘴道:“鸟儿都能垒个窝出来,我就不信,咱俩出手还造不出一间来。”
妲己一听,不服输的劲头儿也升起来,摩拳擦掌地道:“你说的对!幸亏还有点边角料没来得及扔,走,咱们给他造房子去!”
两个人说干就干,兴冲冲地就去给陈玄丘打造豆腐渣工程了。
……
陈玄丘与玉衡骑着马,并肩行于长街之上。八名玉衡的亲信弟子散在四周,把他们悄悄地护在中间。
玉衡扫了眼陈玄丘,微笑道:“陈大夫深受天子宠爱,如今位极人臣,又如此年轻,实在难得。却不知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呐,老员外、老夫人不接来中京享清福么?”
陈玄丘叹道:“陈某是个孤儿,自幼便被弃之荒山,幸蒙师尊收养,迄今不知出身来历。”
“哦?”玉衡的眼神闪烁了几下,道:“这么说来,足下这姓氏,是随了令师么?”
陈玄丘摇头道:“却又不然,这姓呢,就是在下生父的姓氏。”
玉衡眉头一挑,满面疑惑。
陈玄丘道:“家师曾在我的襁褓之中,见到家父留下书信一封,所以知道我该姓陈。”
玉衡面皮子一紧,脱口问道:“信中难道不曾交代你的身世来历?”
陈玄丘苦笑道:“如果有所交代,我也不至于无亲无故了。”
玉衡的脸色又渐渐松驰下来,道:“原来如此,这般看来,你的亲生父母抛弃了你,应该是有难言之隐。那信既是你生身父母留给你的唯一东西,还当好好保存,也有个念想。”
陈玄丘淡淡地道:“信中一切,都是家师口述于我,我并不曾见过家父的留书。”
玉衡诧异地道:“却是为何?”
陈玄丘道:“家师说,山居中虫鼠泛滥,被盗嗑毁去了。”
玉衡:……
陈玄丘扭头看了他一眼,忽然笑道:“我听师父说起这个理由时,也与玉少祝一般无语。”
玉衡叹了口气,苦笑道:“可惜,如此说来,足下身边竟无一件令尊令堂的物事可供追思了。”
陈玄丘下意识地摸了摸他颈间的那块玉佩――“价值连城”,目中一抹奇光一闪而没。
玉衡状似感慨前行,眼角余光却在瞟着陈玄丘的神情变化,瞧他在胸口捏了捏什么东西,心中陡然一动,把这个发现,暗暗记在了心里。
……
御道长街上,一行人马逶迤而行。
队伍的最前边,打着姬字旗号。
这一行人马,正是姬侯进京的队伍。
陪同进京的人马很多,旗帜也很多。
王子启和王子衍亲自去了临潼,陪伴他一起回的中京,二人也赫然打出了自已的旗号。
此外,还有姜家等一些公卿大夫派去的代表,也都走在队伍当中。
这就是姬侯所说的民心所向!
这些人很不满殷受试图废奴的国策,还有一部分是对之前的废除人殉强烈不满。
姬侯是姬国国君,且是西方诸侯之长,是大雍的重臣。
因此,你一日没有说他是个反贼,旁人隆重出迎,便不算过错。
你纵然心中不喜,顶多不予提拔,却也难以因此降罪。
而公卿大夫都是世袭,都有各自的封地,不升迁对他们来说,损失也不是特别大,因而许多人毫无顾忌地加入了迎接姬侯的队伍。
他们相信,以姬侯之贤名,绝不可能有野心。未来会证明,他们才是忠心国事,真正为大雍天下殚精竭虑之臣。
一些公卿没有远迎,但队伍入城后也纷纷赶来。
姬侯高卷轿帘,昂然入城,没有一丝遮掩。
但有公卿来迎,便停车上前相见,这一路走走停停的,队伍越聚越长,半个朝廷都有人站在姬侯的队伍之中。
蜚蠊、马潇、沈洄三人袖着手儿站在路边茶楼上,开着窗子漠然地看着街上。
偶尔会有风来,吹落檐上的雪沫子,撒进屋里来。身材单薄、比较怕冷的沈洄就缩一缩脖子,把他的裘领儿再拉紧些。
在他们身后,两个账房跪坐在几案前,每人面前都摆着文房四宝。
马潇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窗外,飞快地念着名字:“东史宋秋,贞人冯志,下大夫乔杉……”
他后边那个账房笔走龙蛇,记得飞快。
另一边,沈洄一双贼眼在人群里飞快地穿梭着,也在漫声念着人名儿:“小耤臣楚熙宁,多亚官罗义,中大夫何自在……”
蜚蠊负着双手,嘴角撇着,冷笑连连。君上励精图治,年轻有为,偏有许多不开眼的,要拥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跟君上抗衡。
这么多人护着姬侯进京,这是想给大王脸色看么?记下来,全都记下来!不怕你们闹得欢,老子给你拉清单!
嘿嘿,我正愁杨东彬之后不知该拿谁开刀呢,来!把你们的旗号打得更明显些!
御街再往前,便有一座大酒楼。
今天这座大酒楼被人包下了。
偌大的酒楼里边空荡荡的,只有中间一席,正有两位客人在吃着火锅。
陶制的鼎形器皿,鼎下燃着炭火,鼎内沸水滚滚,各种佐料上下翻涌。
酒楼里刀工最好的厨子站在旁边一张案席旁,桌上摆着后院里刚刚屠宰,只晾了两刻钟,肉质稍稍冻硬的大块羊肉,使一口刀,把那肉片儿切得大小均匀,薄厚一致。
切好的羊肉,便由旁边小厮盛在堆了冰雪的盘上,再端到桌上。
费仲和尤浑穿着锦缎单衣,挟一口肥瘦相间的上品羊肉,在沸水中涮得几涮,再往韭菜花、芝麻酱和芥茉拌好的调料里一蘸,吧嗒一口肉,滋溜一口酒,吃得满面红光。
大门外,一个侍卫急急走来,叉手施礼道:“两位大夫,姬侯的车队就要到了。”
“哦?”费仲斜着眼睛向他一瞅,抓起酒盅,一仰脖儿把酒干了,筷子往桌上一拍,大声道:“来啊,把杨东彬提出来,当街行刑!”
尤浑站起来,带着三分酒意晃着身子往前一走,双臂一张,角落里两个侍卫各提一件紫貂的皮裘赶过来,把貂裘往他们身上一裹,两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