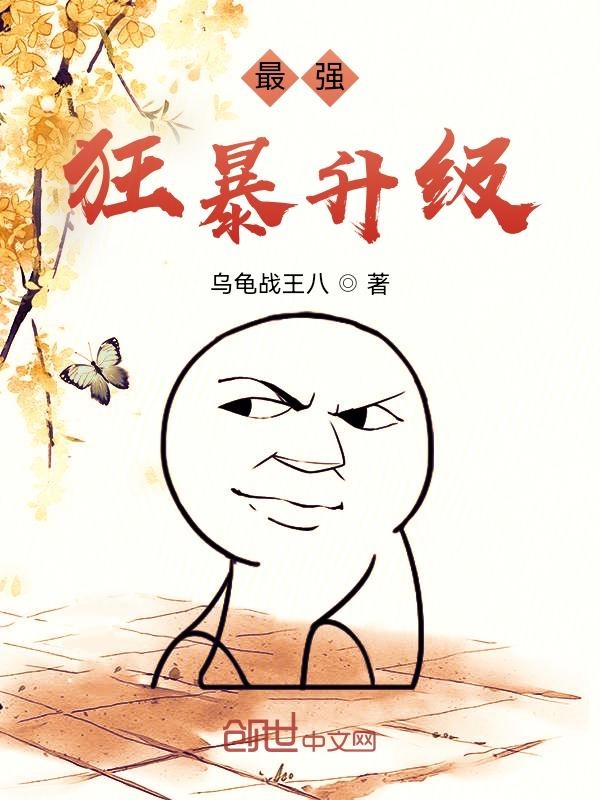“婉儿!”袁裕宁要下床,却被袁裕骢拦住。
他们兄弟两个自小就是一文一武,张弛有度。袁裕宁书卷气重,不要说现在是有病在身,即便是健壮的时候,论起拳脚来,也不是袁裕骢的对手。
方婉儿怕他们争执起来对袁裕宁不利,就强撑着站了起来。她不知道外面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大动静也没人进来。
她早就猜到了袁裕骢的狼子野心,所以已经防范了,那么多护院,为何一个都不见,难不成都被杀了?袁裕骢连他一母同胞的亲哥哥都想杀,并且还觊觎自己的嫂子,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
“你到底怎样才肯放了我们?”方婉儿站直身子,冷声问。
“放了你们?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从来不打算放过的人,只有他一个。而你,依然是裕记的少夫人。”
“你这个疯子。”
“我疯,还不是被你们给逼的?我爹就看中他,小时候我们一起读书,有位先生说我的天分好,学什么都很快。可我爹说他是长子,所以就得注重培养他。其实也无所谓,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虚名,我一直都清楚,袁家终究有一天要在我的手上。这是他怎么读书,父亲怎么培养他,也不能改变的事实。”
方婉儿这么多年没少和形形色.色的商人打交道,比寻常女儿家淡定许多,甚至一般的男子都比不上她的心性。她冷静的同他做交易:“你如果杀了他,即便袁家的一切都属于你了,但你在背后还是会受人诟病,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你愿意放了他,我可以带他离开,把你要的都给你。”
袁裕骢哈哈大笑,冷声道:“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要你,也要袁家的一切。”
“你做梦!”方婉儿一把抽下头上的簪子,狠狠抵在了自己脖颈的动脉上,一字一顿的说:“你若是敢伤他,那我就陪他一起去。”
袁裕骢狠狠的瞪着她,咬牙切齿。他动手拉下床幔,撕成条状,然后把袁裕宁的两只手背绞在后面。方婉儿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怒道:“你放开他!”
“这么多年了,他病了,你却依然一心一意的对他。你就没有想过,其实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吗?因为长幼有序,所以你就嫁给了他,你看看,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哪一点能比得上我。”
袁裕骢步步逼近,方婉儿已经退到了墙角。她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让她什么都顾不得了,她一用力,簪子就陷进了她的皮肉里,却没能更进一步。
袁裕骢紧紧握住她的手腕,笑的像是来自地狱的邪灵:“方婉儿,你这是在跟我表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玉就在你面前,这么多年是你眼盲爱错了人。”
方婉儿和他力气悬殊过大,簪子掉到了地上,艳红刺目的鲜血顺着她雪白的颈子流下,无端妖艳。
袁裕骢眼底有血腥一闪而过,他拉住方婉儿,让她靠在自己怀里,轻声道:“你不是骄傲吗?不是放不下他吗?那就让他看着,你怎么变成我的人!”
方婉儿的眼眸愈发惊恐,她嫁进袁家这么多年,袁裕骢从来没见过她露出这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她所有的笑和泪,似乎都是为袁裕宁而生的,和他扯不上一丝一毫的关系。
现在他就要她承受,不论是爱还是屈辱,方婉儿所有的情绪都应该是因袁裕骢而起。他动手扯她的衣衫,看着她绝望地哭,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疼痛。他忽然发现,自己那么想要得到她,却又那么不想让她受苦。
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他太了解她了,如果不断了最后的念想,她这辈子都忘不了袁裕宁。她不是骄傲么?那他就摧毁她的骄傲。她不是想一死了之吗,那他就让她恨之入骨,让她连死都舍不得。
互相报复,互相伤害互相纠缠,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宿命。虽然有些残忍,但袁裕骢不后悔,他就是要方婉儿永远都摆脱不了他。
本来已经陷入无限绝望的方婉儿身上忽然一轻,然后她看见袁裕宁拿了他的外衫裹住她,又用一方洁白的手帕按在她脖子的伤口上。
刚刚发生了什么,方婉儿都没有看清楚。这时候她才看向周围,一水的黑衣护卫,足足有七八个,门外还有几十个人,押着袁裕骢的随从。她不解地回头,半仰着头看向袁裕宁,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哪来的?”
袁裕宁低头,他的脸色还是很苍白,声音也依然很虚弱,却异常让人安心:“你忘了?这就是你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训练的那批押货的人。”
袁家的生意还是很广的,有时候护送药材就会被人惦记上。起初他们家都是脱镖局给押送,但是后来,镖局有人坐地起价,制肘着袁家。袁裕宁说,不能一直受制于人,所以就暗中培养了这些人,据说都是有功夫在身的。
后来他就病倒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她既要料理裕记的生意,又要照顾卧病在床的他,早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如今,这些人出现了,为什么?
方婉儿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袁裕骢的所作所为早就被袁裕宁看透了,而且他也可以制止,但是,为什么要撑到现在?为什么不在袁裕骢一进门的时候就制止他?
她的眼眸睁得大大的,看着袁裕宁。然后从他平静沉默的神情中,她终于确定了自己刚刚的猜想。他什么都知道,也早就有应对之策。她的声音沙哑,变得又轻又冷:“我安顿守着院子里的人,是你打发走的吧!”
“是。”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对。”
方婉儿觉得他这两个简单的字,已经让她的世界坍塌。她是个远嫁的人,这么多年来,她一个人忍受着思乡之苦,忍受着父母不在身边,忍受着她夫君卧病在床,忍受着她小叔虎视眈眈。
公爹说:“我老了,裕宁怕是不行了,裕骢是不堪重任的,袁家以后就要靠你了。”
方婉儿对她的夫君又敬又爱,她觉得就算是做了寡妇,她也要为他守好袁家,这是他的心愿,也是公爹的信任托付。再苦再难的时候,她都咬牙撑着,不停的给自己加油打气。
可如今呢?袁裕宁为了他心中对袁裕骢的最后一丝不舍,就让她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他知不知道,刚刚若不是袁裕骢反应及时,她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方婉儿眼前的一切渐渐变成灰色,她轻声道:“那你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袁裕宁沉默。他虽然病着,但眼睛不瞎,很多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包括袁裕骢的野心贪婪,包括他对他妻子的觊觎。这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亲弟弟没有任何留恋。
只是,毕竟是一母同胞,母亲又去的早,他如何忍心?但凡是袁裕骢有一丝悔改之意,他都会放了他。所以他才想好好看看,结果是让他失望了。
方婉儿同他夫妻多年,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也知道他这么做的用意。可是谁又能弥补她心上的伤?今日在场的这些护卫,哪个没有看到她落魄狼狈的样子?
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女子身上,都是毁了她的名节,让她一辈子翻不了身,抬不起头。他一心爱着的袁裕宁,就用她的名节甚至是生命去冒险了。她忽然对自己产生了质疑,这些年来,她是不是做错了?
袁家,值不值她付出一生?
袁裕宁,值不值得她爱?
“婉儿…”袁裕宁欲言又止,他去拉她的手,却被她挥开了。
“我觉得我的过去,就像是一场笑话。袁裕宁,你现在不是应该好好同你的亲弟弟叙叙旧吗?我不打扰你们,先走了。”方婉儿紧了紧身上的衣裳,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些护卫们低了头,他们不敢看主母衣衫不整的样子。袁裕宁想追上她,但身子不允许,他往前走了几步,就开始剧烈的咳嗽。他压下喉咙的血腥味儿,大声道:“方婉儿,你给我回来。”
“回来?”方婉儿停下脚步,转过身看他,她笑着说:“你我夫妻一场,我自问从未薄待过你,即便是你卧病在床,也是一心照顾你,给你求医问药。如今,袁裕骢让我受了如此大的耻辱,我要他死,你做得到么?”
“不要任性。”
“你觉得是我任性?”方婉儿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她说:“你和他是一母同胞,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你都觉得可以原谅。说白了,就是兄弟是手足,妻子如衣服。你失去了我,大不了再换一件新的,而你失去了他,却成了终身残疾。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不对。”袁裕宁艰难地道:“即便是妻子如衣服,我这这辈子,也没打算换过。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这是我当年的承诺,我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