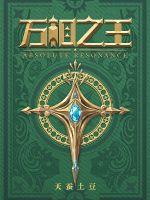“——再喝它一家店!继续喝!不不不!别说一家,就是这整条街,老子也能给它全干喽!嘎哈哈哈哈!老子可是最强的酒豪呀……!”
“是是是。”
“蠢蛋!皮皮皮皮普!别在那儿只知道是是是!是是是的、就好像、那个……就像那啥!哄小孩儿吗!和乖乖儿听话一个意思是吧!你懂不懂啊,嗯!?懂不懂!”
“我懂。我懂——”他用肩膀撑着已经七扭八歪的卡塔力,“但是,已经应该回去了。”
“回个屁啊!回……回去、喂!回哪里啊!混蛋,老子可是那啥,是候鸟啊,什么回去……嚯、嚯、之类的……你让老子回哪儿去啊,回去、老子还能……回哪儿去啊……呃咕……”
稍微有些不知所措,为了表示安慰,他只得在卡塔力的脖子根上轻轻拍了几下。
也许应该不要再管他比较好。
卡塔力垂着头开始号哭。“……成呀,老子我呀,其实根本、不在乎。朋友就朋友、不是挺好的嘛……好个屁啊!哪里……哪里好了啊、白痴!烂死了好嘛,烂透顶了好嘛!老子为什么总是碰上这种结果啊……到底为毛啊……?到底是什么鬼……”
库拉那得欢乐街的夜晚,浓重的色彩与气味混合交杂,凝聚成这里特有的风味。
从昨晚八点开始已经喝遍了四家店,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
他自己倒像是个无底洞,不管喝多少酒都不会醉。但卡塔力不同,虽然酒量并不差,但也不算特别强。而且,这家伙将各种各样的酒混在一起依次喝了个遍,如同要将自己淹死在酒缸里一样,到了明天一定会非常难受。这话暂且不谈,要是再让他喝下去,说不定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先回家吧。”他对卡塔力说。
他做好了哪怕被拒绝也要强行将卡塔力带回住处的心理准备,不过卡塔力闻言只是一边哭着一边点了点头。
“……是嘞。抱歉呐,皮普。这么……麻烦你……陪老子……”
脑中浮现出几个单词,却不知该如何将它们流畅地组合起来。
很想传达心中的情绪,却无法使其清晰成型。
他一直无法习惯共通语,说到底,将思绪以语言传达出来这件事,本就不符合他的习性。
像野兽一样才适合他。
于是他只能摇了摇头。“——不用道歉。”
将卡塔力送回公寓,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不知为何,转到了别的方向。
虽然觉得奇怪,但作为杀人道具被制造出来的他,比起自问自答,更习惯于听任身体自己行动。
回到库拉那得,在街边酒摊点了一杯烧酒,一口气喝干。这种酒是由名叫龙舌兰的植物叶子中榨取的汁液酿造而成,他对这种味道很是中意。
真是不可思议,自己居然对食物饮料有了喜好。
“同样的种类。请再给我一杯。”
有些迫不及待。
杯子递到手中,他又一次一饮而尽。刚将酒杯放下,还没点第三杯,老板便已经递了上来。这一次他只喝了半杯。
说到底,自己并非是什么正经的人,就算想要如常人一般生活,也必定无法实现。光是伪装就已经很难了。
就算能够靠近,也一定会停在某个界限无法更进一步。
越是接触到同伴们的喜怒哀乐,便越是察觉到。
果然自己只不过是希罗克涅的作品罢了。
他将第三杯剩下的部分抿干,对酒摊老板说:“结账。”
付过钱离开酒摊,感觉不到酒后的迷乱,他的本性不允许身体变成那样。
即便是此时回家,啾大概也会出来迎接,那会使他感到安心。
但他无法抑制地觉得,就连这安心感也是虚假的。
呆立着吞了一口唾沫。
“……吉娜?”
什么。
刚才,我、
看见了什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一瞬间,是个女人。兜帽前沿遮至双眼,朝着自己走来。抬起头,瞄了自己一眼,又向左拐去。
夜灯昏暗,他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看清。但是,兜帽下露出的头发看上去的确是土黄色。还有那副容貌。说来可笑,只有一次——明明无数、无数次地肌肤相亲过,他却仅仅见过一次她的脸,因为她总是戴着遮盖容貌兼口枷的器具。他已经记不清了,记不清又怎样。
他冲了上去,步伐有些不稳,难道是喝醉了吗。胸口如同被撕碎,但他仍进入了她最终隐没的阴暗小巷。
不在。
她不在,也没有任何人在。
能看到数个霓虹广告牌,也许她进入了其中某一家店。
又也许,全都是他的错觉。
他突然想到——
不、是恢复了理智。
她已经不在了。
叮嘱他活下去,随后便死了。
他突然察觉到,一双鲜艳的橙色眼瞳正盯着自己。
“……怎么?”
“呀,其实没怎么——”
玛利亚罗斯坐在茶几上,几乎与他膝盖顶膝盖。
现在坐在沙发上的他,之前到底做了什么,竟都忘记了。
玛利亚罗斯歪着头挠着头顶。“……没事吧?总觉得,你好像丢了魂一样。”
“丢了、魂……”他笑着拍了拍胸口,“没有丢。我还活着,就在这里。”
“这句话可不是那个意思哦?”
“那么,是什么意思?”
“嗯……”玛利亚罗斯站了起来,又在他旁边坐下,“你大概是几点回来的?”
“时间……”他环视客厅。
啾擦着餐桌桌布,看样子像是早餐之后,正在收拾打扫。
自己是什么时候坐在这里的?在这期间,玛利亚罗斯他们应该已经吃过了早餐,也许还向他搭过话。
但他不清楚。
完全没有印象。
他低下头。“……时间、记不清了。”
“你去和卡塔力一起喝酒了对吧。”玛利亚罗斯将手放在他的腿上,“啊,我先说清楚,这可不是在责怪你。像我这种人也没有资格担心皮巴涅鲁,所以只是问问而已。”
“是。”他将脸转开,抿紧了嘴,“——是的。我和卡塔力·去喝酒。应该是……喝到两点左右。然后,送他回去。”
“嗯?然后呢?直接回来了……?”
“没有。”
“哼……”玛利亚罗斯跷起二郎腿,食指在他的大腿上轻轻敲击,“那个,抱歉哦?这话可能有些冒犯……那个、你有没有谁……比起‘谁’、应该说是‘哪里’,自己一人的落脚之处、之类的。”
“你说——落脚之处?”
“哎呀……”玛利亚罗斯稍微鼓起一边脸颊,又用手挠了挠,“该怎么说,你看——干脆明说好了……有没有女朋友?”
“女朋友。”
立即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现在说起来有些不合时宜——卡塔力总是‘好想要个女朋友哇好想要个女朋友’地说个不停。
胸中有些发痒。
像是沙子的触感。
他缓缓摇头。“没有。”
“是么……”玛利亚罗斯轻咬着嘴唇将手从他腿上挪开,收回的手又开始隔着衣服摸自己的锁骨,“——呀,我觉得,其实有也没什么奇怪的……吧?有那种感觉、好像是有——这么说可能有些失礼,感觉你的样子有些奇怪呐。像是和谁,发生了什么似的……”
“没有。”他的嘴巴擅自动了起来,“什么都没有。”
“既然你这么说——”玛利亚罗斯虽在微笑,眉头却并不舒展,“那就好。”
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
在家吃过晚饭,本应该回到房间睡觉。
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身处库拉那得。
不,其实并非是没有意识。离开家的时候,还刻意细心地隐藏动静,连啾都没有察觉到。
问题是,自己到底为何要这么做。
他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总之身体这么行动了,于是他便遵从。不过,又是什么催动了身体呢。
还是回家吧。不行。
根本挪不动脚。
在酒摊上又点了三杯龙舌兰烧酒,站着依次喝干。全身包括脸上都布满刺青的酒摊老板前来搭话:“你昨天也来过吧。”
他盯着老板的脸看了一段时间,直到老板挪开视线重新开始工作,他才点了点头。“是的。”
老板没有再看他。“——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烦心事……”他开始品第四杯,“为什么这么问?”
“你顶着一副烦躁的脸呀。”
“脸(译注:这里用的是ツラ,与后文的假发(ヅラ)发音相似。)……”他歪着脑袋挠了挠头顶。
老板看了一眼这边,露出狰狞中带着一丝亲切的笑容。“你听成了假发了吧。怎么,你是戴假发的?”
“天然的。”
“也是呐,看上去就不像。顺便一提我啊——”老板掀起头发,“我是假发。这玩意儿,还蛮贵的呢,看上去挺像回事儿的吧?”
顺势喝了第五杯、离开酒摊之后,身体又一次擅自行动起来。
走在夜晚的库拉那得街道上,周围热闹如同白昼。
大声招呼男性行人、动不动就挽上胳膊的女人们,却从不碰他。
他虽站在这里,却与不存在无异。
时而停下脚步环视四周。
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在寻找着什么。
也察觉到了自己的愿望。
吉娜。
我想见你。
这愿望无法实现,他当然是明白的。可是,他并没有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
“——皮巴涅鲁?”
“呼哎咦?”
被玛利亚罗斯呼唤名字,才清醒过来。
有什么味道。金属的味道。嘴巴里含着硬物,是勺子。坐在椅子上,面前的餐桌上摆着盘子,其中还剩着三分之二的咖喱饭。
玛利亚罗斯已经吃完了,盘子吃得干干净净,现在正喝着橙汁。啾和露西在厨房。多玛德君则横躺在沙发上,一边挠着肚子一边大打哈欠。
“没事吧?”玛利亚罗斯眼神中透着担忧。
他点了点头将勺子从口中取出,吃了一口咖喱饭。已经放凉了,而且很咸。
“……今天的咖喱是失败作。”玛利亚罗斯瞥了一眼多玛德君耸了耸肩,“话说,本来就只会做咖喱,居然还做失败了……真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负责今天伙食的是多玛德君。最近多玛德君看上去很疲累,不论早晚都光是在睡觉。虽然玛利亚罗斯说了可以由他来代班,但多玛德君拒绝了。结果端出来的却是这种东西,玛利亚罗斯显得很郁闷,内心里一定非常介意。
不仅是这件事,最近,玛利亚罗斯似乎心事重重。虽然没有听他本人抱怨过什么,但能够感觉得到。
不想给喜欢操心的玛利亚罗斯再添加多余的麻烦。
他吃光咖喱饭,将盘勺端至厨房,餐具由露西和啾清洗。
本打算回自己的房间,却又重新坐在了椅子上。
“我说皮巴涅鲁啊。”玛利亚罗斯用杯底不断敲着桌面,“……是不是、那个啥、是不是很难和我交流啊……”
“没这回事。”
“别。”玛利亚罗斯稍微嘟起嘴巴,“不用对我客套。”
他垂下头。“……我没那个意思。”
“抱歉,抱歉。”玛利亚罗斯流露出一丝笑容,“我不是说想让你全都告诉我哦?每个人恐怕都有不想告诉别人的事。该怎么说……呀,反正,这只是因为我很任性,与其说想让你告诉我,其实只是我想站在听人诉苦的立场上罢了。”
“任性——”他立即摇头,“不。不对。我觉得·这不是任性。”
“是吗——”
“是的。”
“既然这样,你能全都告诉我吗?”
“唔……”
“开个玩笑啦。”玛利亚罗斯笑着说。
听起来像是发自内心的笑声。
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把心里话和他说清楚吧。
但现在不行。
连他自己都搞不懂自己,根本无从整理心绪。皮巴涅鲁试着一个人思考,却连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甚明了。不,他其实明白,只是无法理解。
吉娜留下让他活下去的遗言死去了。
被人杀害。
他失去了吉娜。
那么,吉娜对于他而言究竟算什么呢。
每当从杀人的工作中归来,她都等着他——不,是满足他的渴求。他抱过她——不,是如同排泄一般将欲望发泄在她的身上。恐怕她也不是自愿的,只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做。这是她的工作,她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任务。
不知是哪一次,她哭了出来。
他不想让她哭,告诉她希望你不要再哭了。
她便抱住他,他听见了她的声音,她的话语。
那个时候她究竟说了什么,如今却几乎全都不记得了。
记忆溶解在时间长河之中,已经无法分辨出原形。
她到底为什么,要让他活下去。
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定要如此强调。
他寻遍了库拉那得,自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于是又不受控制地前往那家酒摊,点了龙舌兰烧酒。满身刺青的老板没有多言。他将第一杯一口喝干,将第二杯放在眼前。
有人在靠近,他虽察觉到了气息,却完全不在乎。
肩膀突然被人一拍,他吃了一惊。
回过头来,发现是卡塔力。“哟。”
卡塔力大摇大摆地坐在他旁边,向着老板伸出食指。“给我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呀。”
“到底是哪个?”老板紧逼着询问。
卡塔力“腐……”地一笑。“一不留神,就只会说‘那个’了呀。虽然是第一次来这家店,却觉得像是老熟客一样啦。抱歉抱歉,原谅老子吧。”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黑加仑!苏打!”
“……居然是鸡尾酒,还是软饮。喂,你是女人么。”
“你这做生意的话还真多呐!老子从一开始就打算点黑加仑苏打啦。最近,这就是My Boom的玩意儿呀。老子爱点什么就点什么,成不成?”
“随便你喽。”老板迅速地调出黑加仑苏打,“拿去。”
“对客人态度要好一点懂不懂……”卡塔力刚喝了一小口,便突然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虽然觉得这个动作很是不明所以,但他却无法将卡塔力的胳膊拨开。
为什么做不到。
明明只是伸手之劳。
“没事儿。”卡塔力晃着他的肩,“就算你什么都不说,也没事儿。当然啦,如果你想说的话,说来听听也无妨,老子随时奉陪。如果你不想说……如果说不出口的话,不说也没事儿的。”
他的目光落在玻璃杯上。“好。”
“喝吧。老子会陪你的。”
“好。”
他将杯中剩下的酒喝光,又朝老板看去。
“那么,我也要一杯黑加仑苏打。”
“——啥、为毛啊!”
“好嘞。”
黑加仑苏打对他来说太甜了。
甜过了头,变成了苦味。
曾经的那一片沙漠。
是他出生以来便映在眼中一望无际的风景,如同他碎裂的内心,如同他的整个世界。
干枯燥热的沙海之中,也曾有一朵花悄然绽放。
那是你,只有你才能——
你到头来还是迅速凋零,洒落于沙海,从我的手中滑脱。
然而我的胸中,至今仍留着一份湿润。
想要呼唤你的名字,即便无法传达,也想要呼唤你。即便无法实现,也想要与你相见。
这份情感无法命名。
正因为明白了它的由来,理解了它的含义,才更加难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你已经不在了。
就算查明了这情感的真相,也无法再与你相见。
可我同样无法抛弃一切,就这样沉没于沙海。
吉娜。
我曾那么爱你。
这一定便是我还存在于此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