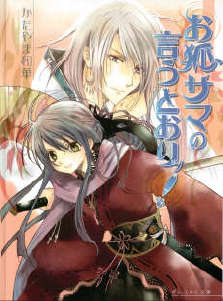(听说初吻的滋味就像「柠檬」,不知道是真是假?)
桐绪依偎在高大的纱那王怀里,挺直腰杆等待着那一刻。
……………………………………………………等啊等。
(奇怪。)
这就怪了,等了又等,怎么自己的唇还是感受不到温度?
(人在初吻时总是自如此焦躁吗?)
举竟这是第一次,所以桐绪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等啊等。
什么事都没发生。
等得不耐烦的桐绪偷偷睁开一只眼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纱那王的脸庞离自己近到不能再近,几乎都要碰到睫毛了。
然而,他的眸子却没有看着桐绪。他的银色眼眸狠狠地瞪着桐绪后方的那片黑暗,彷佛早已将桐绪抛至脑后。
「纱那王?你怎么了?」
「一群杀风景的家伙。别躲了,出来吧。」
纱那王的声音隐含着怒气,响彻了萤光点点的岸边。
是风吹拂着夏草、使它们发出沙沙声吗?还是那群不速之客躲在那儿造成的声响?抑或是上述两项都是原因之一——?
一群手持白刃的恶徒于焉现身。
「刀!?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这晚没有月光,但萤光就足以照亮四周。定睛一看,桐绪认出了这群男子。
「你们不是白天来踢馆那些人吗」」
眼前的三人正是虎背熊腰的扑克脸男、尚称俊美的男子以及狸猫巨汉。其余的两人可能正躲在别处。
「纱那王,你退下!这里太危险了,就交给我吧!」
桐绪白天让他们吃足了苦头,现在他们应该是来报仇的吧?——若真是如此,那正好,我就让你们铩羽而归!
(可恶,把我的少女情怀还来!!!)
程咬金光挑他们两人情意正浓时前来打扰,这让桐绪怒不可遏。
纱那王睁着一双跟色的眼眸,冷静地睥睨着这群男子。
「先是装成试刀子,接着又来踢馆,现在又来趁夜偷袭?居然干出如此下流的勾当,你腰间的玉钢想必正在哭泣吧。」
「试刀手?咦,难道袭击千代小姐的人和踢馆的人是……」
「是同一群人所为。」
「不会吧!」
「兄长已经事先忠告过我了,他说得果然没错。老天,姊姊真会给我添麻烦。」
桐绪听得一头磁水。松寿王说了什么?翠莲王又怎么了?
「纱那王,那个……你能不能说得简单易懂些?」
「这伙人是柳羽藩士。」
「柳羽?你是说将军家的剑术指导柳羽!?」
柳羽藩是纱那王来到风祭家前的上一任主人。桐绪越来越不懂了,为什么柳羽家要盯上桐绪……?
「失禨了,纱那王大人。」
带头的扑克脸男往前站出一步回答。
「得以拜见您的尊颜,在下惶恐至极。久仰大名,在下是柳羽藩士生野传右卫门。」
「客套话就免了。」
「是!我等无意触怒纱那王大人,但为了柳羽家,我等必须消灭风祭桐绪。」
「你们这群人还是一样野蛮。」
纱那王面露轻蔑之色,将视线转向男子们后方茂密的枇杷树林。
「茶茶姬,出来。我知道你在那儿。」
(茶茶姬?)
桐绪随着纱那王的视线望过去,只见过了采收时期的枇杷树荫下有个穿着红衣裳的人正在蠢动者。那是谁?
桐绪不自觉想要往前迈步,但却被纱那王一把拉了回来,跌进纱那王怀里。就在这时——
「风祭桐绪,离纱那王大人远一点!」
「啥?」
桐绪不禁感到目眩神迷。眼前这个人的衣裳比桐绪更加轻柔、缀上了更多蕾丝,而且还有一头蓬松的栗色卷发;她,美得宛如欧罗巴杏的洋娃娃。
「快离他远一点!我不允许你这种下贱的女人碰触纱那王大人!」
「下贱……你太没礼貌了吧!什么意思嘛你!」
「唉呀,好可怕。」
听到桐绪反驳,佳人故意缩起身子,将栗色卷发缠在手指上绕了绕。
「既下贱又粗野,你比传闻中更像个男人婆。」
「传闻,什么传闻啊!?我才不是男人婆,我是女人!」
「你不用这么大声,我又没耳聋。连爹爹都没骂过茶茶我呢。」
她那嗲声嗲气的做作嗓音听得桐绪浑身不对劲,而且桐绪也看不惯以第三人称自称的人。看到桐绪气呼呼的,佳人马上笑盈盈地迎向纱那王。
「纱那王大人,我好想您喔。我找了您好久呢。」
「有事吗?我可不曾允许过你们来晋见我。」
纱那王冷冷地俯视着轻柔的佳人。
「请您回来柳羽家吧,纱那王大人。翠莲王大人也觉得很无奈,为何您要跟着这种穷酸道场的姑娘呢?」
「茶茶姬,桐绪是我的主人,我不准你侮辱她。」
「茶茶才是您的主人!」
这句话桐绪可不能充耳不间。
「你不要胡说八道!纱那王的主人是我才对!」
「纱那王大人是茶茶的狐仙,你快把他还给我!」
「他是我的狐仙,是我一个人的纱那王!」
桐绪宛如想将纱那王藏起来般地站到他面前,这时茶茶姬——
「唉呀~」
竟然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
「男人婆小姐,你不知道吗?茶茶可是纱那王大人的未婚妻呢。」
「……未婚妻?」
「是呀,茶茶和纱那王大人的小指已经被红线紧紧相连在一起了。」
「红、线……」
鹦鹉学舌般地喃喃自语的桐绪,缓缓地回头望向纱那王。这张脸庞依旧俊美,他既没有一丝慌乱,也不加以否定。
「纱那王,这不是真的吧?什么未婚妻,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
「这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过去是指什么时候?你们两个曾经订过婚!?」
桐绪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方才她还享受着糖果般的甜美气氛,然而甜美的部分融化后,她尝到的却是酸苦的滋味。
啪沙啪沙!——空中传来了巨大的振翅声。抬头一看,一只红眼乌鸦正遨翔在夜空中,驱散了萤火虫。
「六连! 」
这双乌鸦是纱那王的使魔。桐绪惊呼一声,六连也「巴嘎(笨蛋)——!」地回应了她,停在主人的肩膀上。
纱那王缓缓地开了口。
「柳羽家干下的卑鄙勾当,六连全都看见了。你们就这么看桐绪不顺眼吗?」
「因为、因为!纱那王大人是茶茶的狐仙嘛!」
茶茶姬推开桐绪,泪汪汪地睁着黑糖般的杏眼,揪着纱那王的袖子。
「纱那王大人,和茶茶一起回柳羽家吧。茶茶好寂寞唷。」
「茶茶姬,抬起脸来。」
纱那王静静地将佳人拥入怀中。
「一段时日不见,你又变得更美了。」
「是的!为了纱那王大人,茶茶一定会绽放得比任何玫瑰还要娇艳!」
开心地羞红了脸颊的茶茶姬,就像染上红晕的红玫瑰般地优雅、美丽。这正是一个坠入爱河的人该有的表情。
俊男美女。心头一紧,桐绪忍不住别过头去。
「美丽的玫瑰总是带刺。柳羽的佳人,如果你不想因刺而凋零,劝你别再接近风祭家的人一步。」
「您的意思是,茶茶我还比不上这区区乡下道场的姑娘?」
「我说过了,不准你侮辱我的主人。」
纱那王露出令人陶醉的美艳笑容,轻抚茶茶姬的面颊。
「你想害你这张自豪的脸蛋被毁容吗?」
他的嗓音甜美得宛如述说着甜言蜜语。
然而,说出来的话却令人背脊发寒。
「茶茶姬,你最好别太惹我生气。」
纱那王对茶茶姬低语着。说完后,他甩开茶茶姬,潇洒地转过身去。
「真扫兴。桐绪,回家吧。」
「啊,嗯、嗯。」
桐绪追着彷佛随萤火虫之光而去的纱那王,一边频频回头看了茶茶姬好几次。
这位轻柔的佳人正嚎啕大哭着,几乎要为之崩溃。
×
翌日依然是个晴朗的好天气,天空充满了积雨云,非常炎热。
桐绪趁着中午暂停练习时和鹰一郎聊了昨晚柳羽家的那件事。将千代误认为桐绪而攻击她的试刀手以及蜂拥而入的踢馆者,全都是柳羽家干下的好事。
听完桐绪的话,机一郎将木刀扛在肩上,咚咚地敲打着脖子。
「柳羽啊~嗯——没想到咱们家这么出名,居然会有这种大大名盯上我们。」
「哥哥,这不是重点吧?柳羽家是纱那王的上一任主人。」
「你都说了是『上一任』啦,他现在住的可是我们家。纱那王之前曾说过狐仙长久以来的庇护反倒害得柳羽家沉沦,现在他们只不过是纸老虎罢了。老实说,我也这么认为。」
难得平常温和的鹰一郎会说出这么严厉的评语。
「话说在前头,试刀手那件事让我很不爽。」
「我也是啊。」
「这么多大男人袭击一个弱女子,连黄口小儿都知道这种行为有多么卑鄙。这是武家名门该做的事吗?」
幸好千代是妖魔才没有大碍,万一她是活生生的人类,不知情况会有多严重——想到这里,鹰一郎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那群人。
「哥哥,对不起。都是我害得千代小姐遇袭……」
茶茶姬视纱那王的现任主人桐绪为眼中钉、肉中刺,她似乎深信只要除掉桐绪,纱那王就会再回到柳羽家。
(而且她还说自己是纱那王的未婚妻……)
某个东西又开始在胸口喀啦喀啦地滚动着。
「哥哥,其实……我也不是不懂茶茶姬的心情。」
「你的意思是?」
「他们的手段确实卑鄙,我也认为茶茶姬是个坏女人,但……」
万一纱那王某天突然从我身旁消失——
桐绪之所以想当纱那王的主人,并非想要荣华富贵或金银珠宝。
她只是想要永远待在纱那王身边罢了。
「我一定也不想看到纱那王和新主人在一起的样子。」
「难得口是心非的你会这么坦率,天要下红雨罗。」
「真抱歉,我就是口是心非!」
桐绪气得自顾自地继续挥剑练习。人家在跟他讲正经事,这个做哥哥的却老是乱开玩笑。
「桐绪,你也觉得纱那王是个好男人吧?」
「是吗——我只觉得他是个臭屁的色狐狸!」
「你看看,你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
鹰一郎边拨乱桐绪的头发边说道。
「你可别让柳羽家的大小姐抢走纱那王喔。长相赢不过人家,那么就用你那越嚼越有劲、跟鱿鱼乾没两样的魅功跟她一较高下吧!」
「我真搞不懂你是夸我还是损我。」
「鱿鱼乾可是下酒菜中的横纲耶!桐绪,别输给她。」
「那还用说!我怎么可能输给她嘛!」
看到桐绪摆出往常的好胜表情、挺直腰杆,鹰一郎不禁露齿大笑,就地盘腿坐了下来。今天没有风,道场内相当闷热,桐绪也汗流浃背地跟着抱膝而坐。
「嗳,桐绪。我们家跟荣华富贵沾不上边,但自从纱那王在这儿住下来之后,生活突然变得好充实。 」
「是呀,每天都像祭典一样热闹。」
「我们遇见了松寿王,也遇见了千代,得到了许多美好的缘分。」
「哥哥,你应该在提到松寿王前先提到千代才对呀。」
「嗯?为什么?」
说了也是白搭,桐绪只好挥挥手催促鹰一郎继续说下去。
「听说这阵子柳羽藩的将军家剑术指导一职可能会被解任。」
「咦!?可是这职位他们连续担任了二百零一年耶!」
「看看他们现在堕落成什么样子,你就不会觉得意外了。」
江都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当今的柳羽家无论是在剑术上或是为政上都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以往上至将军家、下至贵族子弟都到柳羽道场习剑的柳羽家,如今已变得岌岌可危,过去的权势彷佛过往云烟。这对没有出产什么名产,只能靠剑术来支撑经济所需的柳羽藩来说,无疑是生死交关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连将军家和贵族们都已经放弃剑术了?」
「不对,将军家就算再怎么腐败也算是武门之家,即使现在是太平盛世,他们依然会学点剑术皮毛来撑场面。」
「那,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有其他大名想抢走剑术指导这个位子。」
「抢走,这……」
柳羽家会一路沉沦至此,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狐仙的庇护吗?桐绪想起纱那王那双银色眼眸,更用力地抱住了双膝。
这时,鹰一郎彷佛看穿妹妹心思地说道:
「柳羽家可能认为自家的没落是因为纱那王带走了好运和钱财,但事实上或许正好相反。」
「相反?」
「这一点,有跟柳羽家正面交锋过的你应该最清楚吧?紫淀也说过,那些人的刀法中根本没有『心』。」
「没错……」
来踢馆的那群人。他们的每一刀都没有灵魂,如果那种程度已算是他们的真本事,那么确实称不上有实力。
「也就是说,他们仗势着纱那王带来的荣华富贵而忘了在剑道上下苦工……我想大概是这样吧。」
「……也就是纸老虎?」
想当狐仙的主人,必须不断向自己的狐仙展示出主人的器量才行。纱那王的眼睛可以看穿一切,那种仗恃着狐仙的庇护而不知长进的纸老虎是无法驯服纱那王的。
「豢养狐仙就像双面刃,沉溺其中反倒会自取灭亡。柳羽家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沦落至此,因此纱那王才会离开柳羽家吧。」
对于鹰一郎的话语,桐绪深深地点了个头。
(不知我是不是够格当纱那王的主人……)
就像纱那王看破柳羽家而找上桐绪这个新主人一般,他或许现在也看破了桐绪,正打算寻找下一个主人。
——即使身在此刻——
桐绪也总忍不住将茶茶姬嚎啕大哭的模样叠上自己的身影,感到坐立难安。
桐绪向兄长道了声谢,走向纱那王的房间。
自从昨晚赏萤火虫回来后,纱那王的心情就没好过。他和桐绪几乎没说上半句话,只是一迳地在房里生闷气。
就连今天早上,他的表情也实在称不上高兴。这位狐仙大人本来就讨厌早起,早上臭着一张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纱那王,你在吗?」
天气闷热无比,庭院中的蝉也嘈杂地鸣叫个不停。纱那王在扶手上托着腮帮子,似乎对蝉鸣声感到很烦躁。
「吵死了,走路不要那么大声。」
「啊——抱歉。」
桐绪静静地坐在纱那王面前,悄声吩咐在走廊上闲晃的家鸣们去她的房间把扇子拿来。
家鸣们穿越墙壁到隔壁房帮桐绪拿来了印着牵牛花图案的扇子。桐绪接过扇子,缓缓地朝着纱那王扇风。每扇一次,纱那王的衣袍就会飘出伽罗的香味。
「我问你喔,纱那王。关于……昨晚柳羽家那件事……」
「别担心,我相信柳羽家今后不会再做出愚蠢的勾当了。」
「不是啦,我是说,茶茶姬她……」
纱那王以一双宛如森林湖水般静谧的眼神望着欲言又止的桐绪。
每当这种时候,纱那王总会直直地望着桐绪。桐绪总觉得纱那王似乎看穿了她心中那块连自己都看不见的皱折,不禁打了个颤。
「桐绪,茶茶姬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果然没错。」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况且这是姊姊擅自帮我决定的婚事,我本人从未认可过。」
「是雅阳小姐……原来如此。」
桐绪回想起那位宛如朱红朝阳的红发佳人,不禁意志消沉。以前桐绪迷失在妖魔之道时曾遇见这位名为雅阳的人,她是纱那王的姊姊翠莲王,同时也是个重度弟控。她认为桐绪这个穷酸道场的偷腥猫,偷走了她爱护有加的弟弟。
(我才没有抢走纱那王呢……)
现场一阵沉默。
现在是无风的午后,但屋檐下的风铃却忽地发出了沁凉的叮铃声;趁着这个机会,桐绪再度开了口。
「暧,听说柳羽家的剑术指导一职或许会被解任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啊……其实也没什么啦……」
「你该不会想叫我回柳羽家吧?」
「不行!纱那王是人家的狐仙!」
——我不想要你离开我!这股不安的心情,该如何传达给纱那王呢?
「纱那王,我……够格当你的主人吗?」
「这种事情需要问吗?」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茶茶姬她一定也……」
「烦死了。」
纱那王加重了语气,烦躁地在掌心敲响了桧扇。走廊上的家鸣们被这个举动吓得肩膀发颤,踢了拉斗一脚后便逃窜到沙罗双树栏间里了。
「桐绪,你是特地来这儿说废话的吗?」
「这事儿很重要,才不是什么废话呢!柳羽家原本是受纱那王庇护的家族,而茶茶姬也曾经是你的未婚妻,不是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都说别担心了,你只要乖乖点头称是就好。」
「我才不要点头呢!」
桐绪越是反驳,心中越产生一股白费功夫的烦躁感。每当桐绪想对纱那王说出心里的感受,这位高贵的的狐仙总是翩然闪避。
「桐绪。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跟着你?你怎么会不懂呢?」
「我就是不懂嘛!你不说我怎么会懂!」
「那你就打开心眼。」
他的嗓音既低沉又冷淡。说完后,纱那王便托着脸颊不再吭声。
这个时候的纱那王就像他初到风祭道场时一样,是那么的顽固又令人捉摸不定、冷淡无比。
(什么嘛,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有多难受!)
两人背对着背,默不作声。天气更炎热了,庭院里的蝉依然不停地鸣叫着,听得令人心烦气热。
不如过了多久——
「男人婆,原来你在这里啊——有客人喔——!」
当人形化丸探出头来时,桐绪跟纱那王正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老实说,桐绪想离开房间却苦无藉口,化丸的出现正巧给了她一个机会。
「客人?别跟我说又是来踢馆的。」
「是栗金饨啦。」
「啥?栗金饨?」
桐绪边说边步出难搞的高傲狐仙的房间,化丸忍不住一脸担心地拉住桐绪的头发。
「桐绪,你又跟纱那王大人吵架啦?」
「我没有跟那只狐狸吵架啊,只是语言不通而已。」
「蠢才!你别老是惹纱那王大人生气!」
这点桐绪心知肚明,而且她也不是专程过去找他吵架的。她只是既不安又不满,因此忍不住就心烦气躁起来。
(都是因为纱那王闭口不谈……)
心眼。如果桐绪不打开心眼、好好面对纱那王,她永远也读不出纱那王开口不谈的真正心意。
×
会客室里装饰着夏季字画、夏季花草以及鹰一郎昨天去阿佐草寺参拜回程时在骨董市场(据千代所言,他被骗了)买回来的超值高丽青磁香炉(十之八九是赝品)。虽称不上气派,但看来也颇为雅致。
当桐绪跟着化丸来到会客室时﹒赫然发现坐在末座上的竟是……
「你不是弓弦公子吗!」
「咦,桐绪阁下!?为什么你在这儿!?」
「什么沩什么……这里是我家呀。」
「咦!!!」
抬起眼镜一脸震惊的,正是那名不适合在腰间配刀,倒适合抱着书本的削肩青年,也就是前几天在三国桥的金鯱瓦馒头大胃王比赛中被桐绪打败的亩弓弦。
「这样啊,想不到你竟然就是……」
「就是……什么?我怎么了?」
弓弦支支吾吾地望向庭院,于是桐绪也不由得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却彷佛冷不防地挨了个巴掌。樱花树下的章火和木通正团着某人绕来绕去,而那个人正是从昨晚开始便在桐绪脑海中萦绕不去的倩影。
「茶茶姬!?为什么你在这里!?」
「近来可好?男人婆小姐。」
「我是桐绪!」
「唉呀,真对不起。桐绪小姐。」
轻飘飘的衣裳加上蓬松的栗色卷发。阳光下的茶茶姬那艳丽的容颜,洋溢着高贵优雅的气质。
「桐绪,你是弓弦的朋友?」
「嗯——该说是朋友吗?我和他是在前几天的金鯱瓦馒头大胃王比赛中相识的。」
「大胃王比赛?」
看到茶茶姬锁着眉头玩起自己的卷发,桐绪只好挥挥手改变话题。
「不提我了,茶茶姬,你跟弓弦公子才是朋友吧?」
「弓弦是茶茶的监护人。」
「监护人?」
「公主,请入座,站着说话对桐绪阁下太失礼了。」
弓弦对茶茶姬招了招手,而茶茶姬只是停止玩弄头发,偏着头说道:
「我也很想这么做呀,可是这种充满灰尘、霉菌和穷酸味、小得跟牢房没两样的会客室到底有没有打扫干净呀?」
听到这番话,桐绪不禁脸冒青筋。
「如果你看到银色长发掉在地上,那真是对不起了。」
「银色长发……?」
「是呀,我说的是纱那王的头发啦,呵呵呵呵。」
被桐绪这么一刺,茶茶姬一脸不甘心地鼓起腮帮子走进会客室,若无其事地在榻榻米上摸索着银发。她这副模样其实还挺可怜的。
今天鹰一郎并没有出现在会客室,反枕说他今天被自身番的师傅们找去下将棋了。怎么偏偏挑这时候不在,真不愧是芋头老哥。
「弓弦公子,这是怎么回事?茶茶姬的监护人……你究竟是……?」
「这……我也很不希望咱们以这种形式再会……」
弓弦以手帕拭汗,正襟危坐、将手贴在榻榻米上。
「在此重新自我介绍,我是柳羽藩江都家老之子,亩弓弦。没想到你就是纱那王大人的新主人……」
「弓弦公子你……是柳羽藩江都家老的公子?」
「什么嘛喵,原来你不是个普通的肠胃虚弱四眼田鸡喔?」
「化丸!不可以这么没礼貌!」
桐绪训斥了双手交叉在脑后、大摇大摆坐下的化丸,弓弦大大地摇了摇头。
「桐绪阁下,快别这么说,需要道歉的是我们才是。我已经从公主那儿知道了来龙去脉,今天是特地前来赔礼的。试刀手、趁黑偷袭……这种作法实在是太可怕了……呜噗!」
「哇、弓弦公子!?」
弓弦面色铁青地掩住了嘴。
「不、不好意思。我不止讨厌吃甜食,也很怕血腥的话题……」
「弓弦,振作点。你这样还称得上是柳羽家的男子吗?」
「对不起……」
茶茶姬的态度丝毫不像是来道歉的。她十足像个任性公主,还对代替自己低头的弓弦施加压力。
这时,千代端出了羊羹和颜色非常淡的茶水。得知袭击自己——不,得知想要袭击自己当作妹妹看待的桐绪的试刀手出自柳羽家后,千代的态度使变得非常粗鲁。
「为您送上粗茶。」
——她竟然这样说。桐绪望着眨了眨眼转头离去的千代,笑着说道:「千代小姐生起气来还真是可怕呢,」
「桐绪阁下。」
「啊、是是。」
弓弦拿开坐垫,对着表情一脸认真的桐绪磕了个响头。
「袭击桐绪阁下,就等同于和纱那王大人为敌!此次真的万分抱歉!」
「喂,四眼田鸡,如果道歉有用的话,就不需要奉行所啦!」
「化丸,你闭嘴啦!」
「不,化丸阁下说的没错。事已至此,在下亩弓弦只好以柳羽藩士的身分切腹赔罪!」
看到弓弦露出苦恼的表情,桐绪吓得赶紧说道:
「弓弦公子!别冲动啊!」
「……我是很想这么说啦,不过我对剑术实在是一窍不通。」
呃——那你就别说出这种会让人误解的话嘛!
「桐绪阁下,小意思不成敬意,请你笑纳。」
弓弦徐徐地将一个四方形大包袱推至垂头丧气的桐绪膝前。
「这是什么?」
「这是用来陪礼的点心礼盒。」
说是点心礼盒,摸起来却沉甸甸的。桐绪旋即将它推了回去。
「这种东西我不能收。里面装的是小判吧?」
「请你将它当成慰问金。」
「不必了。我们家既没有人受伤、道场的招牌也没有被夺走,没理由收下这笔钱。」
桐绪心想:如果轻易收下柳羽家的钱欠了他们人情,届时就没理由拒绝他们抢走纱那王了。
对于谣传将被解除将军家剑术指导一职、日渐没落的柳羽家来说,与其说他们想要回茶茶姬的未婚夫纱那王,倒不如说他们想藉由天狐之力取回荣华富贵。兹事体大,应该要慎重对应。
「慰问金就不用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弓弦公子,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心意……」
茶茶姬趁着弓弦越说越激动时突然插了个嘴。
「那么,桐绪小姐。为了向你赔罪,茶茶我就跟你做朋友吧。」
「朋友……?」
「你不必因为自己出身于卑贱的乡下道场又没胸没姿色、粗暴又爱吃而感到羞耻,我就大发慈悲跟你做朋友吧。」
她这副自以为是的态度是怎么回事?桐绪想要打哈哈蒙混过去,但茶茶姬依然边玩着自己的栗色卷残边自顾自地说下去。
「茶茶我误会桐绪小姐你了。」
「喔……」
「看到桐绪小姐本人,我终于了解了。纱那王大人之所以离开柳羽家,是因为想要在我俩的恋情中增加一点戏剧性的效果。」
戏剧性?
「桐绪小姐,你有听过一个讲述一名公主在吃下毒苹果后沉睡不醒的外国故事吗?」
「咦?呃——好像有听过吧。」
「就是那个。」
「咦?」
「纱那王大人一定是正在等待茶茶吃下毒馒头而陷入沉眠,这样茶茶就可以在纱那王大人的亲吻下醒来了,呵呵、呵呵。」
「…………………………………………」
哑口无言的桐绪望着弓弦求救,但监护人只是推了推眼镜、满怀歉意地摇了摇头。
「桐绪,别理她。」
化丸边吃着千代端给茶茶姬和弓弦的羊羹边附耳说道。
「茶茶姬以为全世界都绕着她旋转,是个自恋狂。」
「原来如此,真是乐观啊。」
「这只是她自己一厢情愿罢了。本大爷在柳羽家时可是都叫她『爱作梦的栗金饨'哩。」
「栗金饨?啊、你刚刚好像也这么说过。」
「栗金饨是栗色头发的大白痴的简称。」
噗!桐绪忍不住噗嗤一笑。先不谈她像不像大白痴,茶茶姬的蓬松栗色卷发和甜美的容貌倒也和栗金饨有几分相似。
「喂,桐绪小姐,你有没有在听茶茶说话?」
「啊,抱歉。我有在听、我有在听。」
「如此这般,桐绪小姐你并不是我的情敌,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巫婆罢了。既然知道了这一点,我只好跟你作朋友以聊表歉意。」
「啥?巫婆?」
「呵呵呵,就是负责喂茶茶吃下毒馒头的人啦。」
(什么跟什么啊……)
桐绪受到了些许打击。就在这时,在天花板奔来窜去的家鸣们突然消失无踪,而在插着百合花的壁龛中打瞌睡的反枕也睁开双眼、打直腰杆。
「啊、这脚步声是……」
桐绪听到走廊上传来了优雅的衣物摩擦声。走路时能以衣物摩擦声取代脚步声的,在这座宅邸里只有 一人。
庭院中嘈杂的蝉鸣声忽地停了下来,现身的人正是——
「唉呀,纱那王大人!您今天依然如此俊美!」
看到期待已久的狐仙大人登场,茶茶姬不禁又惊又喜。纱那王冷冷地挥了挥手,彷佛想拨散她那热情的热线。他冷酷地说道:
「茶茶姬,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不是说过不准再接近这里一步吗?」
「我跟桐绪小姐现在已经是朋友罗。」
「朋友?」
纱那王随即用那双凤眼瞪向桐绪。
(哇,你也不必摆出这么恐怖的表情嘛!)
桐绪自己也是在一头雾水下硬被她当成朋友的。
看到纱那王现身,弓弦马上毕恭毕敬地双手贴在榻榻米上。
「纱那王大人,得、得以拜见您的尊颜,在下……」
「够了,客套话就免了。」
纱那王斜睨了弓弦一眼,接着又「嗯?」地重新端详了他一次。
「你不就是前几天的金鯱瓦馒头大胃王比赛中的那个男人吗?」
「是、是的!在二国桥时在下有限不识泰山,还请纱那王大人恕罪!」
「你是柳羽藩士?」
「是的!今后还请纱那王大人多多指教!」
纱那王漠然地望着伏在榻榻米上的弓弦一眼,接着将视线移到桐绪身上。
「桐绪,我有话跟你说。待会儿到我房里一趟。」
「哇,纱那王大人的房间!茶茶可以一起过去吗?」
「你还是别过来的好,我房间充满了猫妖的毛,恐怕会弄脏公主你的衣裳。」
纱那王揶揄地笑了笑,说完后便迅速走出了会客室,宛如一阵凉爽的风。
「唉呀~真可惜,人家还没跟纱那王大人说完呢。」
「他是只冷淡的狐狸嘛。」
「就是这样才迷人呀。他对我越是冷淡,我就越想攻陷他。」
「啊,这样啊……」
茶茶姬无视傻眼的桐绪,连珠炮般地从藩邸养的鹦鹉到外国的公主王子童话全都述说一遍后,便迳自回府了。
「好、好累~~~~~~」
在玄关目送茶茶姬和弓弦离去后,桐绪不禁扶着榉木屏风叹了一口气。与其说她对于茶茶姬无厘头的言谈感到无所适从,不如说她觉得完全被茶茶姬牵着鼻子走的自己很窝囊。
「桐绪阁下。」
「呀!怎么了,弓弦公子!」
才刚送走的人现在却突然出现在眼前,桐绪吓了一跳。弓弦似乎是一路冲过来的,他额头冒汗,气喘吁吁。
「我忘记说一件重要的事了!」
「重要的事?什么事?」
「关于前几天大胃王比赛那三十两……」
「啊!」
没错,弓弦是为了买蓝宝石发簪给意中人才参加大胃王比赛的。听到弓弦的苦衷后,桐绪毅然决然地将奖金拱手让给了弓弦。
「多亏你的料助,我买到发簪了。」
「那真是太好了!对方想必一定很开心吧!」
「是啊,她今天还将它戴在头上呢。」
「喔,今天也……咦、咦!?」
桐绪赶紧望向在门口呼唤弓弦的茶茶姬那头栗色蓬松卷发。她的头上插着一支发簪,而松簪上垂着一串葡萄般的蓝宝石。
「弓弦公子,你的意中人该不会是茶茶姬吧?」
「不、不要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令人害羞的话嘛!」
「哇——」
这下不得了了。弓弦的意中人居然是栗金饨公主,这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恋爱之路啊。桐绪看了看弓弦又看了看茶茶姬,忍不住频频感叹。
「桐绪阁下,请你跟茶茶姬好好相处,好吗?」
「呃——这个嘛,我好像不知不觉就变成她的朋友了……」
「公主她其实真的很寂寞。」
弓弦呢喃着。
桐绪注意到他的脸上蒙上了一抹乌云。
「弓弦公子?你这话的意思是?」
弓弦没有答腔,只是取出锁在腰间的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大叫道:
「已经这么晚了!如果不在日落前回府,奶妈阿胜阁下会生气的!茶茶姬和我都被她打了好几次屁股,其凶狠程度简直就像在拍打棉被……」
阿哇哇!
——不知所措的弓弦连忙向桐绪行了好几次礼。
「那么,我就不打扰你了。请代我向纱那王大人问好。」
弓弦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的笑靥虽不像盛开的花朵般艳丽,却有股无名之花才有的亲切感。桐绪实在是无法讨厌像弓弦这样的人。
「祝你愉快,桐绪小姐。」
桐绪再度目送亲昵地挥手告别的茶茶姬和弓弦离去,并且又一次扶着木屏风叹了口气。
×
银河横渡了整个夏季夜空,天空中正高挂着一轮颜色如成熟果实的满月。
太阳下山后白天的暑气依然没有消退,庭院中的各处都有夜蝉断断续续地鸣叫着。
用过晚餐后,桐绪走到纱那王的房间,看到这位狐仙大人正端坐在缘廊上仰望月光。
月亮和黑暗是妖气的泉源。
或者,「月亮」等同于「跟随」?
身为神兽的纱那王和月亮相当搭衬。桐绪在走廊稍远处停了下来,陶醉于纱那王的那副英姿。她不敢上前搭话,只怕破坏了这幅美景。
纱那王察觉到桐绪的气息﹒缓缓地回过头来。
「啊—……抱歉,我打扰到你观月轮了?」
「没有,没关系。」
桐绪被纱那王的俊美吸引而去,宛如飞向火焰的夏虫。她和纱那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正在观月轮的纱那王,感觉好像竹取公主喔。」
「我可不是什么公主。」
「哈哈,也是啦。可是我不禁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使者将你带回月宫。」
那名从月宫而来的使者,其真正身分会是新的主人呢?还是柳羽家?总之,没有人敢保证纱那王永远不会被带走。
桐绪悄悄地揪住了纱那王的上等绢织衣袍的袖子一角。
「桐绪,关于白天那件事……」
「嗯?我真是吃了一惊,想不到那个参加大胃王比赛的弓弦公子竟然是柳羽藩士。纱那王.你在柳羽藩邸时没跟弓弦公子见过面吗?」
「我并没有允许那些家臣前来晋见我。」
这么说来,化丸之前好像说过:当纱那王还在柳羽家时,总是一直待在藩邸后头的一间打不开的房间里,几乎不会在别人面前现身;唯有藩主和茶茶姬等极少数的人可以在纱那王允许时前去晋见、与之交谈。
「别说这个了。桐绪,我想跟你谈谈茶茶姬。」
纱那王摊开绑着色彩鲜艳吊绳的桧扇,由上往下斜睨着桐绪。
「你干嘛跟茶茶姬当什么朋友?」
「这……其实应该说是她硬逼我当她朋友的……」
桐绪嗫嚅着,不断晃动着垂在缘廊下的两条腿。
「她可是柳羽家的公主耶?我不认为她是你这个滥好人应付得来的对手。」
「话是这样没错,可是,弓弦公子都已经如此低声下气地求我,我也不好意思撒手不管。」
「所以我才说你是滥好人。」
纱那王刻意叹了口气,将手伸向太阳穴。
「……这下可中了姊姊的计了。」
「什么?你是说雅阳小姐?」
「算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是你的九尾狐,我只要遵从你的决定、保护你就行了。」
「……你愿意承认我是你的主人?」
桐绪更用力地揪住了纱那王的袖子,这下纱那王终于注意到了。纱那王情不自禁,性感地凝视桐绪的眼眸深处。
就在此时——纱那王身上的伽罗香突然变得浓烈扑鼻,桐绪冷不防被推倒在缘廊上,后脑杓「磅!」地重重撞上了地板。
「好痛……」
「桐绪,昨晚那群不解风情的人坏了我们的好事。」
「咦……」
昨晚,他们两人在萤光点点中独处。
一想起那对若即若离的唇瓣,桐绪便羞得脑袋发热。
「慢、慢着!不行啦,现在不行!」
「为什么?」
「……月娘正看着我们呢。」
仰躺在地的桐绪可以清楚地看见今晚那晴朗无云的满月。这张闪闪发亮的园脸,彷佛正笑盈盈地漂浮在夜空中。
「昨晚我们已经被几十只萤火虫看过了。」
纱那王呢喃着。他的银色长发飘落在桐绪的脸颊上,这般性感的魅力使桐绪不禁目眩神迷,不自觉将视线专注在纱那王那秾纤合度的唇瓣上。
昨晚他们两人在你侬我侬时被打扰,桐绪一直觉得很不甘心。
(要继续的话就趁今晚……)
「纱那王……」
桐绪将指尖伸向纱那王那头一触即溶的银色长发,而纱那王也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桐绪,闭上双眼。」
这句话宛如一句咒语。
桐绪乖乖地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