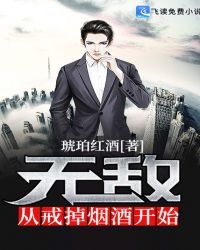恰如日常生活的延续。
大门玲和那些诚心求佛的大婶没什么两样,吃完晚饭登坛诵经。她衣着如常,身穿一件经年败色的连衣裙。空欢喜一场,本以为所谓巫女,会穿着那种服饰呢,结果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她端坐在小屋深处设立的祭坛,用念经一样的词句吟咏着。这是日语吗?我不太清楚。像是经文,却又感觉莫名有一种西洋味道。小屋里是八叠大小的板间,除了祭坛空无一物。巫女身后稍微隔着点距离的,是田城夫妇,此时正弓背敬坐于老旧泛黑的地板之上。
我和康子朝着敞开的入口向里张望,可无论前后都挤满看热闹的人,腹背受迫。有人搭着肩膀往里看,有人趴在地上向里瞅。一时间入口处的长方形区域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脸,就连窗户上也贴上了乡民的脸。就像房中有什么有趣得不得了的西洋景。但无聊。无聊得要死。无聊到犯困。
我固然没有什么过分的期待,但不管好坏总希望仪式中有那么一点刺激。我揉着眼,看着观客的脸,他们一个个身体动也不动,紧盯着房内。有什么有趣的值得坚持下去?只有一个劲儿的诵经般的祈祷。就这样也没法把邪物驱走啊。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这结果,但现在的情形连一点慰借都算不上了,看来只能安慰一下当事人田城夫妇了吧。剥魔仪式可能真的只是个徒有空壳的仪式了吧。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乡民还聚集在这里。他们到底来这儿要看什么,要做什么?
时间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再等十分钟,要是还这样就回去吧。
正这么想着,一瞬间玲停下祷辞站起身。她的大嘴上好像浮现出一丝淫荡的笑,站在田城夫妻面前。
“田城,你应该已经沐浴过了。那么我们开始吧。”
两人身子一擞。不过也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万一比之前的仪式更无聊那该怎么办啊。
田城夫妇站起身,跟着玲走到入口处。突然我的手被人握住了。
一回头,与康子四目相对。“发什么呆呀,准备了。”
“准备什么?”
“做‘场’啊。”
乡民一齐动了起来。大人们小孩们一个个沉默无言各行其是,不浪费一个多余动作,让我感觉大家像是变成了蚂蚁一般的昆虫,心中开始不安。眼看着他们在小屋前围出一个三四层的人圈。格斗场。
这个极小的斗兽场,就是他们所说的“场”吧。
脑海中,浮现出被Glenn叫出去时的场景。那时候教室里的桌椅也围成一个圆形,和现在人群围出的圆圈,原理应该相同。也就是说当时Glenn想对我做的也是剥魔仪式喽?那如果鸟新不来的话,我会怎样?
而与此同时,
有什么正在发生。不吉。
身体围出的圆圈好像魔法阵。田城夫妇走进圆圈正中。
所有的目光如蛇般立起来,扑向两人。站在小屋入口的玲尖声高叫道:
“剥啦!”
接下来的情景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田城努用力地打在妻子脸上。
看得出使出全力了。
女人如陀螺一样转了几圈,猛地砸向人墙,但立刻被人墙推回圆圈中央。努双手掩面后退几步,隐于人圈的纷乱之中。之后从人圈里又出来两个男人,精壮的那人站在佑子身后,双手从她腋下穿上来,十指交叠扣住后颈。这是忧罗希明。他的脸上全无表情,将被固定住的女人面朝向前方。另一个膘健的肥男,开始一拳一拳打在女人脸上。眼看田城佑子的脸变得血迹斑斑。
我小声地问康子:“这什么情况?”
她似恶魔般冷酷地回答:
“这就是剥魔哦。小屋里巫女的祷辞不过是仪式的前段,现在才是主要内容。就跟职业摔角赛一样对吧。”
“你在开玩笑吗!这完全就是暴行,是集团私刑。”
“这就是把魔物剥除的方式啊。”
女人的悲吟飘散在空中。
围观的乡民一个个像蜡人般面无表情,我的脑后一阵阵发麻,汗毛直竖。
从女人口鼻处流出的血,滴滴答答染红了那件白睡裙。肥男又将拳头挥向了女人腹部,一拳一拳偏执地冲进她的身体。
而将女人死死扣住的希明,脸上表情没有一丝改变。
“哎……康子,姑父不是巡查吗?怎么也是个维护小镇治安的角色,也能做这种事?”
“闹祭典,最基本的不就是不分尊卑嘛。”
“祭典?不分尊卑?这帮混蛋。”
“希明姑父是巡查不假,但职业无贵贱,道理上根本讲不嘛。”
“我觉得你是疯了才说出这样的话。”
“少见多怪,只有你觉得是疯了,至少在这个镇子上。”我心内一悚。
这里没有常识。在镇子上,传统是优先于常识的,规矩是休先于道德的。在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面前,巡查也会暴力,善恶轻易逆转。这一瞬间,行使暴力成了善的一面。而这种事本就不应该存在。
康子板着脸,像面对期末考卷一样问我:
“那头肥猪,你以为是谁?就是那个一脸开心地殴打田城佑子的那头肥猪男。”
我的目光回到私刑场。
死胖子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殴打女人。
他滚圆的身体顶着一张巨大的脸,脸上闪着亮晶晶的油汗。随着双下巴每一次颤抖,一拳一拳重复着冲进女人的腰眼。虽然那张脸可以叫做大佛脸,但说不上福相。他的嘴唇有如两条肥硬的红色长虫,正无声地浮出淫靡的笑容。
“那人叫王渕一马,镇长王渕。”
“我们镇的镇长?怎么我只看见一个单纯的变态?”
“肥猪、变态、死人渣。但他也是镇长,还是Glenn他爹。”那个把我叫去的初三生。那家伙叫王渕一也,一马和一也,还继承了他老子姓名里一个字。Glenn也准备像这样把我围在圈中蹂躏一番吧。
暴行愈发过激。
更多人变成了施暴者,现在圈内已经有四个男人,不断踢着倒在地上的女子。她的睡裙已被血污和呕吐物染成红茶色,整件衣服破烂不堪,已分不清是衣服还是血肉模糊的肌肤。
康子的声音如咒语般响起。
“驱除附身魔物,只能给予附身之人肉体上的痛楚。魔物如果无法忍受疼痛,自然无法聚集体内。请看,人面疮正在消失。”那不是消失,只是单纯被打烂了。佑子肩上的赘生物几经殴打烂成一片,化为鲜红的肉块。不,毋宁说女人全身都化为一摊鲜红的烂肉。肩上的伤——如藏叶于林(?)一般——消散在遍体鳞伤中。但是暴行并未停止,剥魔仪式也没有停止,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打死人了,怎么办?”
“凉办。”
康子若无其事地说。我立刻反驳道:
“没道理啊,这不跟杀人仪式一样了?”
“有时就是啊,剥魔仪式跟出不出人命没有关系,它更关心的是恶灵有没有被驱除。如果恶灵没被完全消灭,则可能附身他人。你知道为什么乡下人怕死吗?死亡本身没什么好怕的,可怕的是死后给家人和周围的人增添的麻烦。人一凉,葬礼啊什么的烦都烦死了。说到制造麻烦,当事人会自责到难以忍耐。但被指责之时,当事人都已经走了,真是荒唐。话扯得有点远,但是对于剥魔仪式上死亡来说,是当事人的本愿也是被其家庭接纳的。”
本愿?接纳?“你真这么想?”康子没有回答。
田城佑子的脸上血肉模糊。牙齿基本全折断掉光了,嘴巴仅剩一个空洞。
这样的死法……是本愿吗?被接纳了吗?可以理解吗?怎么可能理解。要让他们住手。我要阻止这一切。让他们停。
绝对要让他们停下来!于是我大步走上前。康子一把抓住我。
“不行!你要搞什么?”
我甩开康子的手,又向前一步。这时。
另一只手扳住我的肩膀,一把将我拽了回来。是个男的。他就这么拽着我的肩膀,将我往人圈之外拉,随手一扔。
我脚下一个趔趄,猛然向小屋墙壁撞去,右肩撞得生疼。我不服输地站起身,重新走向人圈。
接着又被男的捉住,扔出圈外。
跌坐在地。我忍不住大叫。“干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想干什么。”
“救她啊!还用说吗?”
“说什么说!”男人的口气强硬。
这个男人身着西装,年龄不详。梳着大背头,一张脸惊人地端正。目光沉稳有一种老谋深算之感,但外貌更接近三十多岁。他身材精干,行动迅猛,力道也强。无论是运动细胞还是体力我都无法和他匹敌。
女人已经不见了呻吟,是昏了,还是死了?村人们貌似毫不关心我和男人之间的争执,竟没有一人回头。就连站在门口的玲也没往这边看上一眼。
不能放弃。我想救她。
我站起身,再次冲进圈中,但立刻被抓住,扔回墙壁上。他啪啪拍着胸口,像掸去衣服上的灰尘,嗓音清楚地说道:“别犟了,冷静一下。”
我斜眼看了看他,又一次惊讶了。他的脸端正得没有一点瑕疵。秀丽的额头、清晰高挺的美鼻,剑眉之下是一双深思熟虑的炯炯慧眼,凛然抿紧嘴角。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谁会对一个同性看到入迷。
可不巧,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向前迈出一步。
“别挡道。我不去帮,人就死了。”
“但你的力量不够,力量不够只能眼睁睁地在旁边看着。”
“力量不够就只能干站着?我做不到在一边见死不救,而且冷漠也不是好事。”
“你的想法很好,但现在不许乱动,冷静一下。”
“不,我偏要去。”
“不行。这会儿你进去,挨打的就是你,只会再加一个受伤的。如果被杀,命就没了。”
头脑稍稍冷静了一点。道理确实如他所言,但是——“但是,他们那么蛮……”
“忍着,有勇不等于无谋。你现在跳进去就是无谋,而选择隐忍才是勇气。”
“别把怂说成勇气。”
“你以一敌十能赢?还不是被吞。”
“那怎么办才好。你说要怎么做?”
“等。”
“等?”
“剥魔仪式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结束,等人都走光了再去救她。”
“如果到时候人都不行了,怎么办?”
“那没辙,放弃吧。”
“不负责任。还有你说要救,怎么救啊?”
“全力抢救。相信我,我是医生,一定会抢救她的。”
“医生?”
男人直直地看着我。目光中带着忧郁,像要把我吸入眼中。那劝说过几十几百个患者的值得信赖的眼神,此刻正寸步不离地盯着我的双眼。
“相信我,我来治。”
他的目光说服了我的心。
但是脑筋还在轴上下不来。
“我不能接受。你说你是医生,但事前冷眼旁观,事后只看伤治伤完事的救助,就是错的。你如果是个医生,难道不应该趁着伤势还不严重,不,是伤势未来时就把人给救了吗?现在事情拖到这个地步——”
男人眼中闪过深沉而又悲哀的神色。我虽然说得吞吞吐吐,但还在继续。
“如果你是医生,就该中止剥魔仪式。如果想救人,当然要站在她前面保护她。不向传统恶习低头,该破除的就必须得破除。而不是到现在都还闷声不响地干看着。”
我明白这样理论下去不会有结果。无论说什么,这人都一动不动,我只能干发脾气。但是这个自称医生的男人,看起来好像认真听取了我这个小孩子的言语。
我又继续纠缠下去。
“还有啊,为什么你不给那人治疗呢?她肩上那个看起来挺瘆人的,不就是个人面疮吗。实际上,只是个赘生物。现代医学应该能治得好的。那为什么你不在事情闹大之前帮她治呢?”
“抱歉。”
他直率地道歉,说道:
“但如果病人都不来看病,医生也没法治疗啊。他那个妻子从没来找过我。”
这也是事实吧,我理解了,但嘴上还是刹不住。他两手握住我的肩膀,垂眼说道:
“你说的是对的。我心里也认同。但我是个医生的同时,也是‘这个镇子’上的医生。如今不到所有都结束,我都不能轻举妄动。就算有救人想法,就算有治疗技术,不,正因为如此,我比你更心酸,更悲惨,更痛苦。你要理解我。还有,不要做愣头青。等你跳进圈子成了伤者,我还要再多照顾一个。别给我添乱,拜托了。”
他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懂了。
但是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这时,从旁边传来养母的声音。
“结束了!魔物已被剥除了,逃走了,一定不会再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男人的手也静静地从我肩上收了回去。
四目相对。
来到这个镇子,我第一次遇到了可以打心底里值得信赖的目光。
“医生。”我开口道。
“医生,您尊姓大名?”
“差贺显。在一丁目开差贺诊所。”
“差贺……大夫?”
好像在哪里听过。差贺——这个姓确实也是第一次听到。“你是如月琢磨君吧。”
“你怎么知道?”
“忧罗巡查和那个女孩子聊的时候在一旁听到的。”也就是说他是之前偷看我的目光中的一道了。
回过神时,人群已经面无表情地匆匆散去,好像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仪式理所当然的结束而已。
我又将视线转回差贺身上。
“生病或者受伤时,我能去差贺诊所吗?可以吗?”
“当然,但我希望你永远别来,祝你身体健康。”
不知何时,玲的身影已经不见。四周也不见康子、忧罗巡查和王渕镇长,最不可思议的是连田城努都不在了。
我觉得奇怪。“田城努他人呢?”差贺点点头说道:“回去了。”
“就把他老婆丢这儿,这也太过分了。”
“惯例上就是要将驱邪后的人留下,独自回去的。就算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也不能把他们带回去。”
“不能带走伤者?”
“这是惯例。”
“怎么能这样。经过剥魔的人尚能活动的还好,那些被打到动不了的情况怎么办?”
“如果不是相关人员,是可以施救的。只要撑到全部结束。”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林中,不久就剩下我和差贺。
月色笼罩下,佑子像尸体一样被留在这个世界。我俩迅速奔向她身边。她一动不动,如一条烂毛巾,浑身滚着鲜血和污泥,感觉不到任何活气。
差贺查了查她的伤口,又找了找脉搏,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还活着,但不赶紧处理会很危险。要麻烦你帮我了。”
“怎么帮?”
“你抬她的腿,帮忙运到我车子那边。”
差贺轻轻扶起佑子的上半身。我担起她两条腿,开口问起我十分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在哪里听说过你的名字。”
“可能吧。因为我差一点就成了你的养父。”
“什么!”
“你的养母,大门玲。她前不久还叫差贺玲。我是她的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