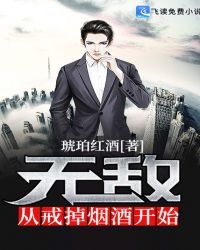是日晚饭时分,我向嘴里塞满酱茄子的法子打听道:“森林里有一个养老院诶。”
我喝了口酱汤补充道:
“从什么时候起那里就荒废了?”
法子一边大口咀嚼一边说话,她的大嘴一张一合,还能看见嘴里黏糊糊的茄子。
“这个还是有点,太辣了啊。不过,味道出来了。那个,养老院?小琢磨真是胡来诶,怎么跑那地方去了。那一块不是什么好地方,最好别靠近。我不是在地图上画得很清楚了嘛。虽说去美术馆也要穿过森林,但入口完全不一样好吧。”
可我的问题一点也没回答。她接着又自顾自地替我做主。
“算了,你去过了也没办法了,要说这个镇子有养老院那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小琢磨没有方向感嘛。”
但是为什么——本想反问,但转念放弃了。还是听法子接下去怎么说吧。
她把饭扒完继续说道:
“那是外人建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笨蛋,说什么看不了镇上的惨状。明明自己什么都不了解,还说什么出于好意,蠢到家了,后来当然就荒废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人住嘛。但是你要说什么时候荒废的,虽然我记不清楚,但也是十多年前了。”
我注意到她那句强烈否定“不可能有人住”,于是开口:“为什么会没人住?镇上不是有老年人吗?”
“这个嘛,养老院不是想住就住的,还得要钱,懂吗?镇上大家都穷,就算想也住不起啊。”
法子眼睛望向天花板。
“而且风水也不好,镇里人是绝不会在那块地上建房子的。大凶之地真的存在哦。唉,搞得饭都吃不香,话题打住不说了。”
“我在养老院里看到过像流浪者一样的一对母子,还穿着红色衣服。”
“没听说过,不是都说了话题打住嘛。那地方只要有个屋顶,就有流浪者会去住。那房子就这么废在那里十年了,也不拆除。不过又不关我事。对了琢磨君,差不多……”
她好像看着我的表情说道:
“我就现在直说了哈。之前我和老公也商量过,肯定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大宅子里。但是我和有里,要一直这么来回跑也很辛苦。而且以我和有里家的条件,谁都没有余力收养你。所以这次就想和你谈谈,看看你能否找到你爸那边的亲人收留,怎么样?”
她强行换了话题。
我放下筷子,回答道:
“当然,我想也是会到这一步的。”她的圆眼睛转了一圈,说道:
“说起来吧,这事情也急不得,还要就着他们的方便。不过我想这是最好的安排了。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小琢磨?”
“是啊。”
虽然我这么说,但事情却不简单。生父老家是开传统料理亭的。我听说在子承父业的问题上,父亲与二老起了冲突,中途像断绝父子关系一般离家出走。虽然我的爷爷奶奶最终应该不会拒绝我,但我想中间的沟通斡旋不会顺利。
但如今我连应付姑姑的气力都没有,像那些烦心讨厌的事情还是再往后放一放。
姑姑看了一圈餐厅。
“你要是不在这边,这房子我们也想着卖了。反正又没人住,我们也管理不来。不如把美术馆里的展品和这房子一起卖掉,还能得一笔财产。”
到最后,原来我可能只是个搅和事的累赘。她眯着双眼。
“那么,由我来和你父亲老家那边沟通联络吧,联系方式给我一下。”
生父老家的电话号码我记在学生笔记本上了,但是笔记本还在不二男那里没还回来。他说没法立刻弄明白纹章的意义,所以我交给他研究去了。
晚饭结束后,姑姑回家了。
我预习了一遍明天的功课,早早地上了床。关上灯,在窗外的虫鸣声中,清静了耳畔的喧嚣。
突然,我想起美术馆里那个叫Aku的男人——就是地狱之门的门卫——的那张脸。低头时,他又长又直的刘海遮住了半边面颊,双眼低垂面色忧郁。那张脸比起接待,更适合站在酒吧吧台里。他自称是个落寞的学者。
在Aku的怂恿下,我调查了过去的杀人事件,
可这和大门玲被害一案有何关联尚不清楚。王渕事件和玲的事件真有联系吗?倒不如说完全没有联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说起来那时候Aku也不一定是知道什么隐情,才劝我去调查陈年旧案。也可能是对我一个小孩极度敷衍了两句。虽说我不觉得他是那种不正经的人,但我又了解他什么呢?光看外表,他那张扑克脸有可能是坏人——但Aku单纯是个奇怪之人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忧罗巡查告诉我有关王渕事件的种种他好像也知道。难道说Aku也许能为我一刀剖开那起不可能犯罪的谜题?就像创造神迹的耶稣基督,又像为华生解开谜团的福尔摩斯。
但是Aku既然有神秘家的一面,也可能会说出下面的话。
——琢磨君,这是镰鼬的杰作啊。越后七大不可思议之一,《北越奇谈》有云:“多有经于社地者,不虑面容手足皮割肉裂,反白甚其事。”就是说经过神社领地的人,毫无感觉之中身体就完全被划破了。多数情况下伤口既不见红,也无疼痛,不知怎地就被割了,故谓之风妖作祟。在其他地域,亦称其“镰风”……
Aku的脸,变成了鼬面。
再一看去,他的双手化作两把巨大的镰刀。
怪物举起镰刀,一瞬之间嚓、嚓、嚓,三名女子的头颅应声掉落。那三人的脸分明是大门玲、京香和美丽……
沙漠里矗立着一座塔。
塔是由巨大的圆柱层层叠叠堆积而成。好像还是砖瓦堆砌。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巨大。仅第一层的底基就能轻松容下五六座大都市。事实上,好像整座塔中也成为了一座巨型城市。
一层又一层,给人一种罗马斗兽场的错觉。巨大的斗兽场上面架着一个小一点的斗兽场。在它之上,还叠着更小的斗兽场。抬头看去,层层重复毫无止休,直冲云霄。
夕阳西沉,一面天空被不祥的烈烈红色所尽染。在那浓得发紫的红色将天空全体染得不见异色之时,最终审判开始了。那号角的红光,将塔全部染红,宛如沾满鲜血。
一瞬间,风声猎猎,沙尘四起。
飞沙走石遮望眼,我揉揉眼睛,泪水簌簌滑落。
在模糊视野的远方,出现了少女的身影,像烈日下的热浪。她妆容好似天使,一袭宽松白裙乘风轻舞,齐肩黑发也随之摇摆。
锐利而庄严的双眼直盯着我。可怕。
可能应该写作畏惧。如此庄严的美催生出我的敬畏。我向少女提问:
“那是巴别塔吗?”她没有回答。我继续寻问:
“这里是示拿之地吗?是巴比伦吗?”
少女的瞳色一变,变得接近灰色,双眼看上去好像只有白眼珠。“这里不是地上,这里也不是地球。”她慢慢地指向空中。
“那红色,不是地球上拥有的颜色。”我看看脚边。
“但这是,这是大地呀。”就在一瞬间,天地逆转。我的感觉反转了。
脚下土地顿时变为穹顶。大地和天空角色调转。
我双脚离开地面,跌入空中。
眼见头上的沙漠越来越远,我不禁放声悲鸣。坠向天空。
再看时,少女在我眼前张开双臂。无声之中我向她求救。她摇头说道:
“这不是坠落,是飞翔。把心放开。”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向云层撞去。云海之中,我手足无措胡乱挣扎。
“两手伸开,坚定心念。”
少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也终于伸开自己的双手双脚,整个人形成一个大字形。
冲出云层,冲出大气层,最后进入宇宙,我终于抓住了飞翔的感觉。
两极四象,亿万恒星,光彩夺目。我在宇宙中跳伞。
与少女在宇宙中共舞。我看见了巨大的金月。
少女沐浴着明月反射的金光,包裹在金色的神圣中,极尽闪耀。就这样飞去月亮该有多好。就我们两人,飞去月亮。
不过行程不允许。
巨塔贯穿宇宙,向更遥远处延伸。我们沿着塔延伸的方向飞去。“快看。”
我望向她手指的方向。巨塔细如丝线的顶端是一颗熟悉的蓝色星球。
地球。
它果然不是巴别塔。巴别塔是从地面直上天际,而这座塔正相反,从天到地无穷无尽地延伸。
少女皱了皱眉,转身面朝天界。我也望向她,问道:“怎么了?”
她尖锐的眼光盯住天界的方向,高声道:“来了!”
那是怎样的凄厉景象。远处的高塔裂开,瞬间化为飞尘,是从我们飞来的方向,从塔的底基崩坏碎裂。宛似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的爆炸,一次爆炸引发了连锁爆发。转眼破坏就奔向近旁,我俩被卷入了爆炸之中。我伸开手似要求救。右手握住了少女的手臂,可紧握的两人立刻撞上一块飞冲过来的巨大砖块,在冲击中失散了彼此。
就在我被冲撞翻转之际,我看见了。那个破坏巨塔的元凶。
它……也如从天界通向地面一般……巨大而绵长……
怪物——的一块鳞片就有学校操场大小——在塔中蚕食鲸吞般地前进,迅猛狂行间,巨塔外壁灰飞烟灭。
恶魔。那是恶魔真容。我突然睁开眼,已经是早上了。不知何时卷入乱梦。于是一个白天,我都在昏沉中度过。
结束功课下午到家后,我去往祖父的偏宅。好久末曾拜访偏宅,水泥地面上堆着几个纸箱子,依然保持着上次的模样。不知怎地我怀念起养母那句责骂——你准备放到什么时候!?于是我开始组装新带来的空纸箱,想接续之前的整理工作。虽然就这么放着不碍事,但心里总觉得难受。
地上又出现了二十多个空纸箱。
我依旧从书架一端依次将剩下的书打包装好。纸张陈旧的气味撞击着鼻腔。都是西洋书。难道都是有关恶魔和魔法的书籍吗?我打开一本,依然读不懂。但是在其中我发现了一副绘有恶魔纹章的插画。久久凝视后,我拿它与地上画着的花纹比对,可惜不是一样东西。我一想到打开的这一页污秽邪恶,慌忙合上书本,放进箱里。
从那以后直到收拾完毕,我都没再打开过一本书。就把它们藏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吧。
我将纸箱搬去储物房。
刚搬了十来个箱子,手臂就酸痛起来。虽说也可以边搬边休息,但我的心里一直悬着,非要一口气干完不可。
当我搬到第十三箱时,突然感觉家里来人了。我看见一个人影横穿庭院,走向大门。
那影子身着红衣,手脚奇妙地多出一副。定睛再看,人影倏地消失了。和在忧罗巡查家时看到的一样。是废弃养老院里那个抱着小孩的螃蟹女吧。
我将纸箱往脚边一放,从后头追了出去。
那女的想干啥?在森林里就在追我,后来出现在巡查家,现在又跑到大门家门口了。一次比一次近,不正常。
只能是跟踪狂。我和她只是在那天见过一面,凭什么屡次追我?一见钟情吗?
我当然不能理解异常的思维,但是也要承认她能直追到我住处,做法虽蠢但运气不错,所以也不可掉以轻心。
真是恶心透了。
仿佛要扫去心中的癔怪,我又回去继续搬运纸箱。我在偏宅和储物房之间往返了好几次。
终于到了最后一箱。搞定!
我将纸箱放到储物房的地面,仰天张开双臂,摆出“万岁”的姿势高喊。
“完事儿了!”剩下的只有空虚。
我期待的充实感连一块碎片也没留下。
在不可名状的空寂之中,好像祖母的身影又跳了出来。那一天大门松悄悄走进储物房,就像消失在黑暗中一般的瘦小背影。我再次放眼室内。
杂物堆积,完全看不到墙壁。最多的是木箱。从德古拉公爵的棺材般的长衣箱、四脚结实的旧餐桌,到大花瓶、电风扇、割草机,什么都有。面向入口的那面墙安放着佛像,但因为围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失损了应有的威严。
那时候祖母来这里干什么呢?还有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她的身影了。她是来找以前的旧物,还是向佛像祈祷呢?双脚自然地向佛像迈去。
真的很旧。佛像上的金箔都掉光了,浑身黑黢黢的。感觉是把镰仓大佛等比缩小为人身大小。他体态端庄,衣纹和缓,面目慈悲。意外地可能出自名家之手。但当我转向佛身背后查看时,发现地板上一处奇妙状况。
一块地板——虽然被杂物堆积得不剩多少地面了——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灰,但佛像的右侧地面却比较干净。这块正好是佛像底座的大小的区域,灰尘被擦拭得很干净。这个灰尘擦痕可能是将佛像连同底座从左向右推动时产生的。
我回到佛像左边,用肩膀抵住佛像。
没有声音,但佛像微微一动。我肩上又加了一把力气。
突然,几乎没有抵抗地,底座向右滑去,其下赫然出现一个漆黑的正方形洞口。
地板上开了个洞。地下室的入口?
洞口只够一人勉强进入,我向里看去,看见了安装在洞里的梯子。但光线照不到更里面,不知深浅。
我跑回主馆取来手电,回到储物房。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手电,钻进洞中。这木头梯子是被千人握万人摸过的吗?光溜溜的感觉像包了层浆一样。
在光线中我一边摸索,一边慢慢地向下走。
比预想要早,我很快就降到洞底,整个梯子也就一层普通房屋的高度吧。
我打探四周,不是地下室,而是一个单纯的洞穴。背对梯子,直径约莫两米的地道向前延伸。光不能及的洞穴,瘆人指数不是手工制作的妖怪屋可以比拟。好像在黑暗的深处,有什么不明形状的东西正哗啦哗啦地朝这边逼近。我被这样的预感侵袭,踌躇中不敢踏出一步。我真想回去算了,可转念一想我特地从主屋取来手电,心里就拧着一股劲儿,向前迈出一步。
前行一阵,身后储物房的光亮已经照不清脚边的路了。我左手扶着洞壁,借手中电筒的光继续前进。
静得只听见自己的呼吸。
为什么喘息声会如此剧烈?明明还没走上一公里,怎么跟刚跑完长跑一样……
我喘了口气。不觉停下脚步。
道路分成两条。原来这条地道还有岔路,难道说这是个如同地下迷宫般的结构?
后颈刺毛毛的。万一稀里糊涂乱闯,不小心迷了路怎么办?会在地道的黑暗里彷徨至死吗?要是死在地道里,怕是化成白骨也绝不会被发现吧。
怎么办?回去吗?
但我还想往前走走,于是选择了左边的那条路。可能因为左边那条路更宽敞一点吧。
但我立刻就后悔了。
因为怪就怪在这条路是条下坡道。每走一步都感觉往地底更近一步。我想象不出这条路最终通向何方。
我蜗行在向下延伸的洞穴,像走在通往冥府的路。到底走了多久?我左手的感觉也渐渐变了。
岩壁开始变得潮湿。
指尖能明显感受到阴冷,这时——啪嗒。
我突然踩进水中。鞋子瞬间湿透。
我汗毛一竖,退后一步。
照亮脚下,可以看见水洼,好像还在微微流动。我将电筒顺水照去,前方完全被淹了,灯光也照不到更远的地方。
恐怕这是涌泉水吧。但我没有继续前进的胆量。水深不测,一步下去尚能着地,第二步、第三步呢?如果水越来越深,该如何是好。
我没想到洞中的积水会如此可怕。
可能实际上再走两步,道路会直转而上,最后通向地面。可能所谓水洼,水深也不过十厘米,长度也就几米的范围。
但在电筒不能窥探水洼全貌之际,要充分考虑到道路无止尽地向下延伸之风险。
可能没多久,洞口变宽,直接连通到一片巨大的地下湖。
眼前的黑暗中,沉睡着一个自远古而来的巨大地下湖。而在这片不知纵横几何的深水湖中,又潜藏着怎样的生物呢?
想象让我心生震撼,活生生地感到毛骨悚然。我不禁又退后几步。
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了,感觉好像正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将要从水边爬出来。
我撒开脚步,一口气冲上坡。头脑角落里突然闪过可怕的念头。刚才过来途中有没有我没注意到的岔路,那我现在还能回到储物房吗?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我就已经落入地下迷宫了?如果兜兜转转再走到这个水洼之地,我会不会绝望地尖叫?
奔跑,透不过气般地奔跑,当我再见到光亮时,呼地松了口气。洞穴只是个简单的Y字形,路程距离也不算远。可怕的是想象力吓自己。能将水洼妄想成地下湖,那是黑暗的力量啊。
我爬上梯子,终于透过气来。我将佛像胡乱地推回原位。
谢了,这样的探索我再也不想玩了,再也不想钻地道了。从储物房里出来,沐浴阳光的感觉真好。
这时祖母的身影又浮现脑海。她真的搬去养老院了吗?还是像我一样,钻进地道了呢?那如果她在那个Y字形的三岔口,会作何选择?
向左走——假设地下湖真实存在,那她难道会自行沉眠在湖底?
而向右走,一定会通往别处——前提是那个分岔不是死路。
而无论通向何处,我都觉得不是一块福地。
因为大门松的身影从那之后,就如烟似雾般消失了。
日本新泻地区的民间传说故事集。
示拿意即吼狮之地,最古之希伯来文,以此名称为巴比伦,后始改称为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