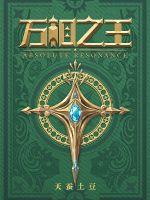老鬼们见识多,经验多,却似乎达成共识,一些秦昆想知道的秘闻并不给他讲。
生死道的家伙大多都是这幅神秘的模样,没想到鬼也是如此。
秦昆没问为什么,也不在意。
第九天的时间,秦昆居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左近臣写的,说秦昆手机关机,联系不上,跟八方渔楼打听,才知道他在茅山。信里,左近臣要求秦昆陪他去一趟魔都。
一天后,金陵车站,秦昆看到了眼圈红肿的左近臣,是李崇、柴子悦陪他来的。
左近臣活死人一样站在原地,也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整个人似乎傻掉了。
柴子悦陪在左近臣身边,秦昆皱眉,看向李崇:“怎么回事?”
他沉着脸,不怒自威,一股气场透体而出。
李崇点起一根烟,唏嘘道:“不是外人招惹,是家事。”
弹了弹烟灰,李崇鼻子喷出两道烟雾:“崔师叔快死了。”
魔都一如既往的繁华。
出站,万人郎开车亲自来接,众人一路开往医院。
黄浦江滚滚入海,江边不远,一个VIP病房中。
窗台上的马蹄莲已经枯萎,整间病房弥漫着死气,医院固有的消毒水味道,在VIP病房里也不能免俗,除此之外,还有腥臊的臭气。
“师祖…”
床边,崔鸿鹄看到左近臣来了,红着眼睛施礼。
左近臣摸着崔鸿鹄的头,一言不发地看向床头。
病床上是判家家主崔无命,真的快无命了。枯槁干瘪的皮肤,躺在那里和一具活死人一样,眼中无神,又显得呆滞,他挣扎着想要起来,牵动着浑身插着的管子,但徒劳无功。
“无命,躺好,师父来看你了。”
左近臣坐在床边,摸了摸崔无命的头。
崔无命七十多,老态龙钟,被他师父摸着头,两行浑浊的老泪流下。
“师父…”
微弱的声音,中气虚弱,几乎没什么进的气了。秦昆环视病房,这里弥漫的不仅仅是死气,还有一股不甘消散的威压。
崔无命,不想死啊…
秦昆站在那里,崔无命松开师父的手,朝秦昆伸了伸,秦昆握住:“老崔,交代遗言吧。”
崔无命脸上泛出愤怒的潮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微弱的枪棒言,像是扫帚把打到了头上,秦昆挠头一笑:“我一般不卖别人人情。真没什么嘱咐的?”
崔无命一怔,忽然有些激动,才明白秦昆这句话的意义。
“鸿鹄命苦…我师父年岁已大…不方便照顾…替我…照顾好他!”
“小事。”
秦昆拍了拍崔无命的手背,没多说什么,只身走到病房外间。
隔着玻璃,左近臣的背影确实苍老了许多,秦昆有些于心不忍。
这就是判家啊。
坚持自己心中正义的宗门。
对他们而言,只要有可能威胁华夏生死道的,皆可杀。
冷血,是否也代表着公正?
“你们先出去,我有些话要对无命说。”左近臣情绪低落,艰难地挥了挥手。
病房外,气氛沉默。
崔鸿鹄的情绪也非常低落,被柴子悦搂在怀里,安慰地拍了两下,就开始大哭。
这是个没有家的孩子。
被左近臣捡到,被崔无命抚养。
判家就是他的家,师祖和师父就是他的亲人。
师父时日无多,勾起了崔鸿鹄心中的酸楚,泪水涌出后,就停不下来了。
柴子悦摸着崔鸿鹄的头,说着安慰的话,不起作用,崔鸿鹄也知道自己的情绪会让病房里的两个老人更难受,哭了一会强行忍住,无声地啜泣起来。
秦昆坐在沙发上,默默点起一根烟。
李崇也坐在旁边。
黑老虎是斗宗最感性的人,虎目泛红,简单的生离死别,带着他尽可能的往坏处想,如果是景三生去世了呢?如果是葛战呢?如果斗宗前辈也这样突然就要走了,他该怎么办?
“秦昆…”
“嗯?”
“景三生他,不会这么轻易去世吧?”
李崇舔了舔牙齿,小心询问。
秦昆道:“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问我这外人,我怎么知道。还和景老虎闹着呢?”
“没有。”
“李崇,你30了。”
“知道。”
“景三生是你亲爹。”
“不是!”李崇忽然开口,“我是个野种。我打听过,生死道里,没几个亲生血脉。”
啪,秦昆抽了他一耳光:“葛大爷给你和景老虎验过血。”
李崇捂着脸:“验血的结果,也可以作伪。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这点捂事实的伎俩,谁没玩过?”
秦昆不想告诉他,景老虎的业火印消失后,可以繁衍子孙后代的。
“就算不是,你准备怎么办?”秦昆再问。
李崇没了答案。
秦昆道:“就算是野种,也有个男人愿意把你养大,顶着你父亲的名号,还不要求你改姓,景老虎没做错吧?”
“他抛弃了我妈。”
李崇底气已经不足了,呢喃了一句,就颓然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算了,你说的不错。我一直不敢面对现实,也没去跟他打听过一些细节。有些事,我到了该知道的年纪了。”
秦昆没有继续纠结这话题,而是陷入长久的沉默中。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成熟,就会变得喜欢思考,很少说话。
秦昆成为了一个看客,在医院陪床三天,直到崔无命去世。
6月中下旬。
阳光正好,但扫不清心中的阴霾。
判家家主崔无命去世,享年71。
崔无命生前没几个朋友,追悼会现场的人也不多。
秦昆,李崇,万人郎,柴子悦,崔鸿鹄,五个人,加上一个更老的老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告别仪式。
殓妆是秦昆帮忙做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叹为观止,有几位入殓师想来请教一番,被李崇瞪了回去。
崔无命安详地躺在那里,像是睡着一样,遗体上是左近臣亲手撒的纸钱。
然后,推入了火化炉。
“人死如灯灭,一抔飞灰一事哀。”
“来世再作伴,共饮美酒坐楼台。”
“魂儿,该飞就飞吧,莫恋人间!”
骨灰撒在黄浦江中,众人听着左近臣自言自语,陪他在作最后的道别。
出海口,海鸟在盘旋,清风拂面。
待骨灰撒完,左近臣收起所有的情绪,看着崔鸿鹄道:“即日起,你便是判家家主。”
“师祖…”崔鸿鹄惶恐。
左近臣抬手制止道:“魔都,老夫再也不来了。有什么事需要助拳,找你的师兄师姐。有什么人欺负你,找扶余山当家的。鸿鹄,你长大了,该飞了。”
左近臣来的突然。
走的也突然。
当晚,李崇夫妇随着他离开,秦昆被安排在这里,照顾崔鸿鹄一阵子。
对此秦昆没什么意见。
出来游玩的,在魔都待一阵子,也可以。
崔鸿鹄刚刚中考结束,原本是一个放松的假期,变成了这样,心情难受可想而知。
叛逆期的孩子如果遭到人生变故,会改变很大。尤其是这种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亲人离世。
魔都,一个六层砖楼。
屋子里摆放的都是老家具。
冰箱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上面的海尔兄弟已经泛白,茶几是没有的。屋子里只有一个折叠桌子,总面积不超过70平。
“你住在那。”崔鸿鹄指了指师父的房间。
秦昆进屋,屋子和阳台相连,养着花草,里面放了一个小木桌,上面铺着毛毡,应该是崔无命练字的地方。
床很硬,老头似乎都喜欢这种床。
墙上挂着遗像,秦昆不嫌晦气,床头摆放着两个相框,一张黑白照片,是崔无命和左近臣的合影,底下的字是‘爱徒十岁,摄于人民公园’。照片里的崔无命骑着木马,笑的非常开心。
一张彩色,是崔无命和崔鸿鹄的合影,底下的字依然是‘爱徒十岁,摄于人民公园’。照片里的崔鸿鹄戴着面纱,骑着木马,笑的非常开心。
“别碰!”
崔鸿鹄看到秦昆拿着相框,站在门口警告道。
秦昆一眼瞟来,崔鸿鹄一怔,呢喃道:“我意思是,别碰坏了…”
“暑假怎么安排?左大爷把我留在这,我觉得应该陪你去转转。”
秦昆将相框放好,征询着崔鸿鹄的意思。
崔鸿鹄道:“你会玩游戏吗?”
秦昆眨着眼睛:“不太会。”
崔鸿鹄扁着嘴:“那就不用了,我不想去其他地方转。”